其實敏銳的電影人對本專業的處境一清二楚,德勒茲直言電影作為「工業藝術」的尷尬境地在於,它既不屬於藝術,也不是科學。電影不過是種左右逢源,時常我們認為它應該承擔某種責任,或認為它應當成為一類瑰寶而不受打擾,可只要人們拍過一些片段就知道,如何讓一群人專心為一個靈感服務,如何獲得一筆資金來為這個靈感的實現鋪好道路,這都不是電影本體的問題。當然,對於觀眾而言,電影就是一段可以在螢幕上觀看的故事,並不復雜,然而如何做一個能讓觀眾滿意或能讓觀眾買帳的電影,卻讓電影人焦頭爛額。不僅與其他電影競爭,還有與其他更快更碎的方式競爭。某種程度上說,最會賺錢的電影人最了解這一電影市場背後的現實,但反過來也成立,他們對現實一無所知,甚至無需所知,只了解現實的反饋即可,例如二零二三是需要依靠與哭泣的一年,所以這一年稱得上優秀或大賣的電影均是情緒販賣機。我想,電影人終於搞清楚電影究竟是什麼了,如果它既不是藝術,也不是科學,它總要是什麼吧。產品?擬像?一種代償手段?簡單一點,就是情感,誰能不突兀地呈現我們在生活中逐漸丟失的溫情與愛,誰的電影就是出色的。我坦言,在十二月看得幾部「高分電影」如《三大隊》《年會不能停》都令我不適,但我更要坦言,「我算老幾?」。所以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電影為什麼會成為這樣?
當然我對此有回答,有太多的理論、研究可以准確地解釋,但相較於解釋,我更想要不斷追問「為什麼」。我承認,每個人都渴望在影像中獲得情感,最精良的剪輯師(沃爾特.默奇)——親手創造電影的人——對此早有經驗:「人們觀看影片最終記住的不是剪輯,不是攝影,也不是表演,甚至不是故事,而是感情,是他們的感受。」我也有在電影中的索求,但稍有些不同的是,畢竟我也算是學過電影、解剖過電影的人,也深知戴錦華所言的准確:看電影的能力是訓練出來的。這不是傲慢,而是理性地判斷。是學習,是努力地求索,像每一個奮鬥者一樣,努力讓自己在所學的領域專業一點。至少我是這麼想的,因而我對電影現狀的不滿,絕不會怪罪於觀眾,而是更為深層、本質的內容被膚淺的截斷了。觀眾是無辜的,對電影熱忱的人也是無辜的。
以下是我分享的二零二三片單,共二十部,分華語與海外。這些電影並不全是去年上映的,包含了很多老片子,像《神女》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作為普通觀眾,有些片子並不出眾但很打動我,所以我將其列進來了,而作為影視的學生,有些片子很精彩,不能不分享。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也祝電影,中國電影,會更好吧。
華語

低賤的不是妓女,高尚的也不是母親,我們歌頌阮玲玉所飾演的「神女」的原因,在於時代悲歌下存留的人性之光。這抹光尚存,就是希望,而她搖曳幾度熄滅,則是現實的寫照。這一現實並不止局限於三零年代的中國,而是存續千年的某種思想,某類道德,逼迫在眾口議論下的女性只能困於「低賤」與「高尚」間左右逢源,弘揚一個女性的偉大,與臆想一個女性的低賤,都只是將她切為兩半,推向兩個極端,而忽視了她自己。梅達爾多子爵①被宗教戰爭一分為二,炮火象徵的暴力意味著「看見」——暴力就發生在人們眼前!而女性的分裂是隱匿的,「天生的」,被默許的。只有當妓女成為一個母親並被看見時,人們才瞭然原來妓女也有母性,可當人們因此為神女的悲劇落淚時,隱匿的暴力才從中顯露:妓女只有被當成母親時才能得到一些無關人士的憐憫,可為什麼女人不能自證?而當我們離開熒幕,回到現實時,倘若你身旁有這樣一位神女,你會以怎樣的眼光看待她?我說過,這是現實的寫照,不僅僅是螢幕內的現實主義,不僅僅是阮玲玉個人命運②的悲劇,而是我們每個人正處於的現實,的寫照。
注釋:
PS:B站上可免費觀看。

在進步電影時期除去《小城之春》外最打動我的一部電影。首先對電影空間的運用,一棟樓內上、中、下層的分化與對應的階級表達,鏡頭在樓梯間不斷變換角度與方向來呈現人物關系與情感,這在早期中國電影中比較罕見。我們知道,電影與城市相伴而生,如何運用精妙的窺視機械——攝影機——去展現城市的原生力量是現代電影創作的必備技能之一,在不同形狀、大小的遮蔽物間窺探人物,以抓住他們的本質,不僅需要拍攝者與調度者,還需要直接暴露在攝影機內的演員。趙丹,相較於三零年代尚且桎梏於舞台框架內的表演,《烏鴉與麻雀》的表演是極具感染力與生活氣息的,盡管他說的滬語,但實在親切,詼諧自然,我在教室里笑得合不攏嘴。
PS:B站上可免費觀看。

我喜歡平靜的電影中流露的詩意,淡淡的香味從綠油油的雜草叢中散發出來,當我看到時,我認為我也嗅到了。我迷戀這種體驗,恰是因為我不知道雜草是什麼味道,我寧願相信一切自然的味道均是沁人的。我覺得,電影可以記錄、呈現,某種失去的生活。逝去與尚未到來一樣,都是當下無法得到,並可能會有的。在這里,「可能」是期盼,是執念,也是詩意的簡述。《城南舊事》中每個人都能看出憂傷,這是電影被設計好的表達,但除此之外,每個人又能偏向另一片境地。曾經爺爺在吃麵時反復咀嚼,說這里頭有小麥的香氣,可我怎麼吃也吃不出來。我從不知道小麥是什麼味道,只知道面澆上不同鹵子是什麼味道。其實也挺幸福的。

《悲情城市》太出色了,在我心目中是華語最佳。華語電影首先要有這片土地上自己的東西,我不是僅僅指代符號與噱頭,我是指真正的、孕育於這片土地上的眼睛與心靈。
為什麼一定要聊這個問題。在分析藝術的內涵時,人們常說「藝術是相通的」,如此重復地評價每一個作品,像是這種「相通」可以唾手可得。然而藝術的欣賞並非是已知結果的向前推導,一部作品頌揚愛或揭露壓迫,而不同時代、地區、種族間有不同的愛、壓迫或反抗的方式與表意之外的情愫。藝術的相通往往是深邃且復雜的,要想了解作品,知識、閱歷、思考是基本前提,因而與藝術作品的交融也是一段漫長的過程。相通,或者說「普世」本就是抽象的概念,而在今天卻因要實現某種度量的統一而擁有具體的形象。例如愛情本身是普世的,可要將其表達出來(在螢幕上,以達到販賣的目的),需要一個共同的視覺象徵。世界上求愛的方式曾數不勝數,如今卻只能以玫瑰數量來判斷「他或她到底愛不愛我」了。
《悲情城市》在參加威尼斯電影節時觀影人覺得這是優秀的電影,但具體怎樣優秀,如果沒有謝晉為他們解釋其中的歷史與細節,那年的金獅獎或許就不屬於它。另一個實例是來自一位日本留學的朋友的,《霸王別姬》在日本重映時他的一位日本老師去看了,但並沒有想像中的那般震撼,原因是她不了解中國,不了解那段歷史,所以作品無法自發地向她展現全貌。電影就在那里,它不會變的,但要看懂電影,可不是件輕松的事情。

不過是個故事吧,你當真就是真,當假就是假,你覺得是男孩的意淫就是意淫,覺得是歷史的悲劇就是悲劇。但也只有孩子才能在悲劇中想像出另一副光景了,不是嗎?而大人呢,即便從悲劇中出來,也很難再看到陽光了。

《槍火》是那種不說廢話拔槍就射的黑幫警匪片,對話精簡,節奏迅速,人物關系的變化幅度微妙,在短時間內建構起情感關聯並在危機中通過「槍」這一主要元素來呈現情感的維系或破損。人們都知道槍是象徵死亡,而已槍械為主題的電影的目的要麼強化這一觀念,要麼豐富槍的含義。《槍火》屬於後者,人隱於槍後,槍便代表了語言,每次開槍,就意味著一次交流。多年後的《神探》杜琪峯將槍語運用到精神分析領域,成為不少熱衷於解碼的影迷們心目中的經典。

輪回。
仇恨的阻斷在於兒子們不會看到殺戮,而宿命往往會以別樣的方式降臨在你頭上。

雖然製作一部紀錄電影(紀錄片)與大多數人想像的不太一樣,不過,倘若你將鏡頭對准了普通人,那就安心讓他們說話吧。放心把你的畫面交付給他們,「生活」就在每一次無意間冒出、翻湧,最終匯成一條綿延不止的長河,直至無依之地。
PS:在中國紀錄片網免費觀看

我一般把電影以兩個標準劃分:專業或非專業;感人或無感。以後者作為評判方式,那麼看電影則是件很私人的事。綜合來說,《溫柔殼》不是一部非常好的電影,但我哭了。在講抑鬱症這個題材時,很少有作品能既不美化又不固化的看待這一病症。我相信主創人員是對抑鬱症群體有同理心的,並了解過他們,試圖還原真實的患者與他們的處境,以喚起觀眾的同情。拍一部好電影其實非常難,要精準地刻畫形象、傳遞情感、最終被觀眾接受,絕非只是「看」與「被看」的關系。我不能說《溫柔殼》做到了精準,但我看到了真誠,這也是很難能可貴的了。
當然也可以看出——又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對於國內文藝片導演的影響。這是個忍俊不禁的插曲。
多說一點,有很多講抑鬱症的片子其實都並不了解抑鬱症是什麼,《溫柔殼》也一樣,不過這是另一維度的事情(需要一定人文社科知識),因為嚴格意義上講,抑鬱症不是「疾病」,而是「現代」的附屬,換言之,是「世界的問題」。所以,抑鬱症患者們要大膽相信這不是你的錯,這就是世界的錯,是我們生下來就被捲入攪拌機中,身心都扭曲了。

其實如果專出一個電影就倆北京爺們聊天或一對北京夫婦聊天,真挺逗的,一個人在電影院哈哈大笑。我很喜歡中年人的北京話,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聽著就很有底。
北京,從我很小時就與它產生了一絲細微的聯系,從它給予的幻夢到展現的現實,中間沒有一抹生活的痕跡。因為我不是北京人,每次進京,都必須飽含一種莫名的激情,無論是新奇還是壓抑。
海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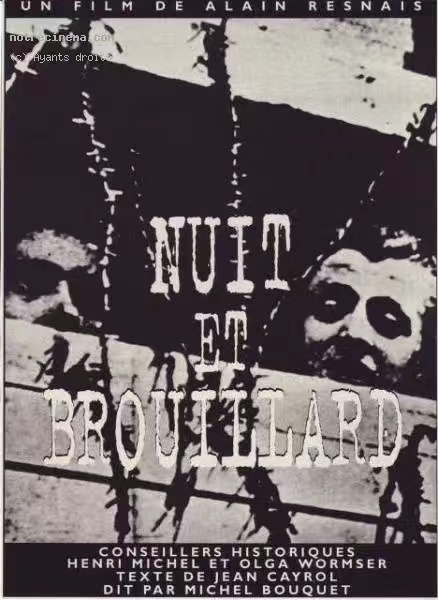
「我們假裝這一切只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發生一次。我們開始對周圍的一切視而不見,對人性的哭喊充耳不聞。」(《夜與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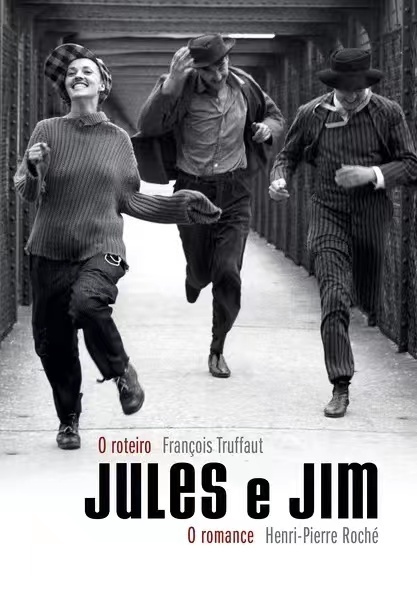
當一部電影的宣傳語是「中國東北的《祖與占》」時,就可以期待它會被怎樣戲弄的了。《燃冬》我沒有看過,實在是因為被這些虛頭八腦的宣傳口號搞得沒了胃口。不是所有的「三人行」都是《祖與占》,《戲夢巴黎》《鳥,孤兒和愚人》或其他什麼片子。在激盪與虛無交融的歐洲,在那個時代,愛這一空無的情感掙脫於舊有的桎梏後的難以捉摸,幾近要將人撕裂、顛倒,再舍棄。將人丟到湖中,遺忘在霧蒙蒙的車站,身子是軟的,而欲望是蓬鬆的。這三隻迷途之鳥不知去哪里歇腳,我想它們最終是累死的。

如果只能推一部戈達爾的電影,我會選擇《蔑視》,這部電影太棒了,是「偉大的失敗」(上映時無人叫好十幾年後贊譽連連)俱樂部的一員。當然,在上海看這部電影前我並不知道這些過去,我只知道我願意為它寫一篇萬字影評。有些電影就是能讓你願意說話,但不能打開這個口子,要不然後面的七部電影就沒什麼空間了。實驗性的、反叛的、成熟的、思辨的戈達爾你都能在這部電影中看到,這傢伙,始終如一。
不過《蔑視》在美國上映時還是有人願意為它說些好話的,比如桑塔格在她的文集《反對闡釋》中就提到(《論風格》),是個彩蛋,書單與片單的聯動。可以看完《蔑視》後再讀那篇文章,會有新的感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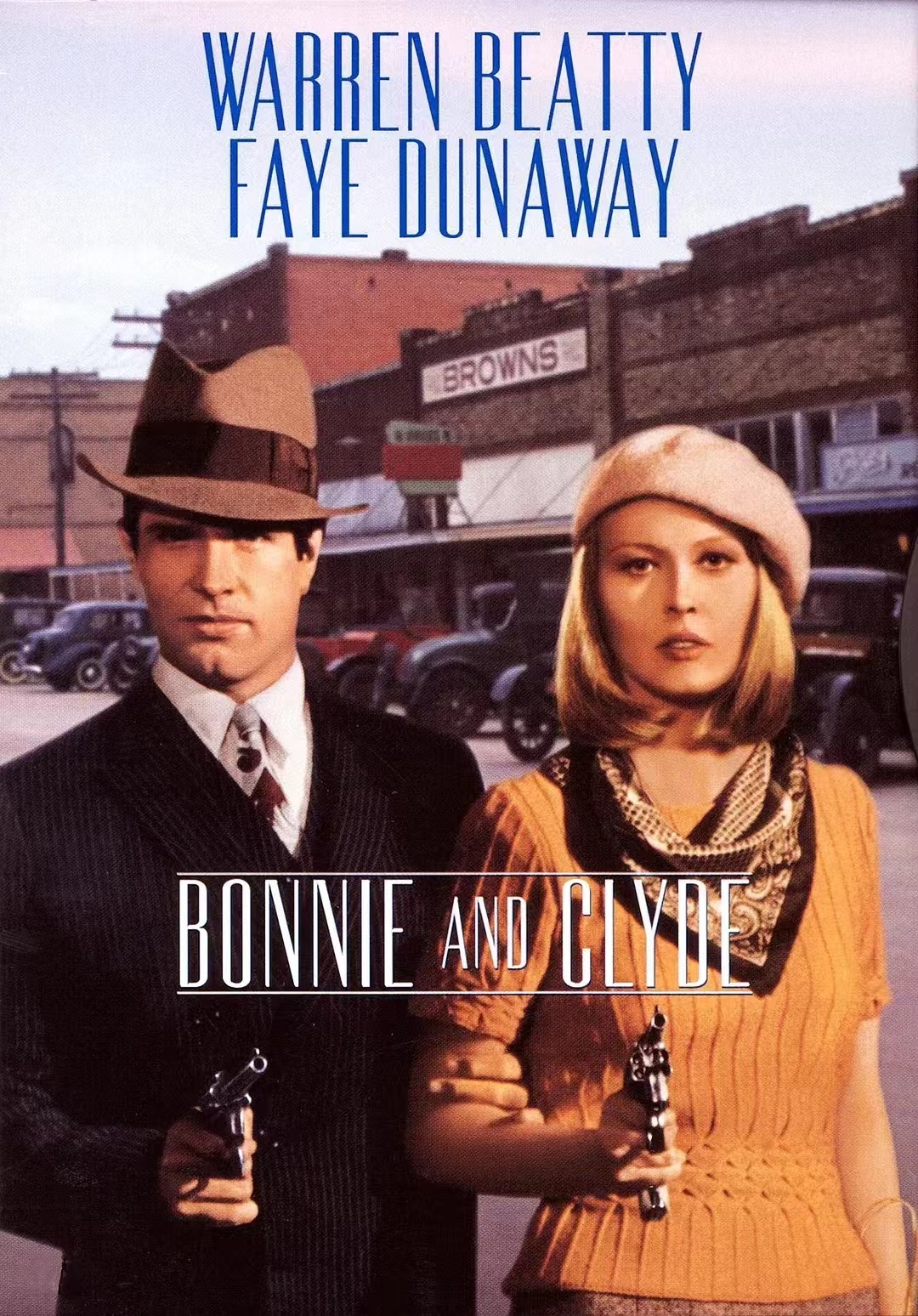
當車輛緩緩開進農民(拾荒者)的駐營時,我想起來《無依之地》的開頭。淚崩。此時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此時是二十一世紀。那些面孔,什麼都沒改變,只是換了一代又一代homeless。那些經驗是,罪犯是壞人,流浪漢是下等人,必須遠離、憎惡、鄙夷。可人們還不明白嗎?是城市親手創造了罪犯,又親手把他們消滅,如同在免疫系統內外生成的細胞一樣,只有這樣才能被視為「生命」。只不過我們的說法更有意義:主持正義與公平。總要有敵人,才能有正義;只要有貧窮,才能有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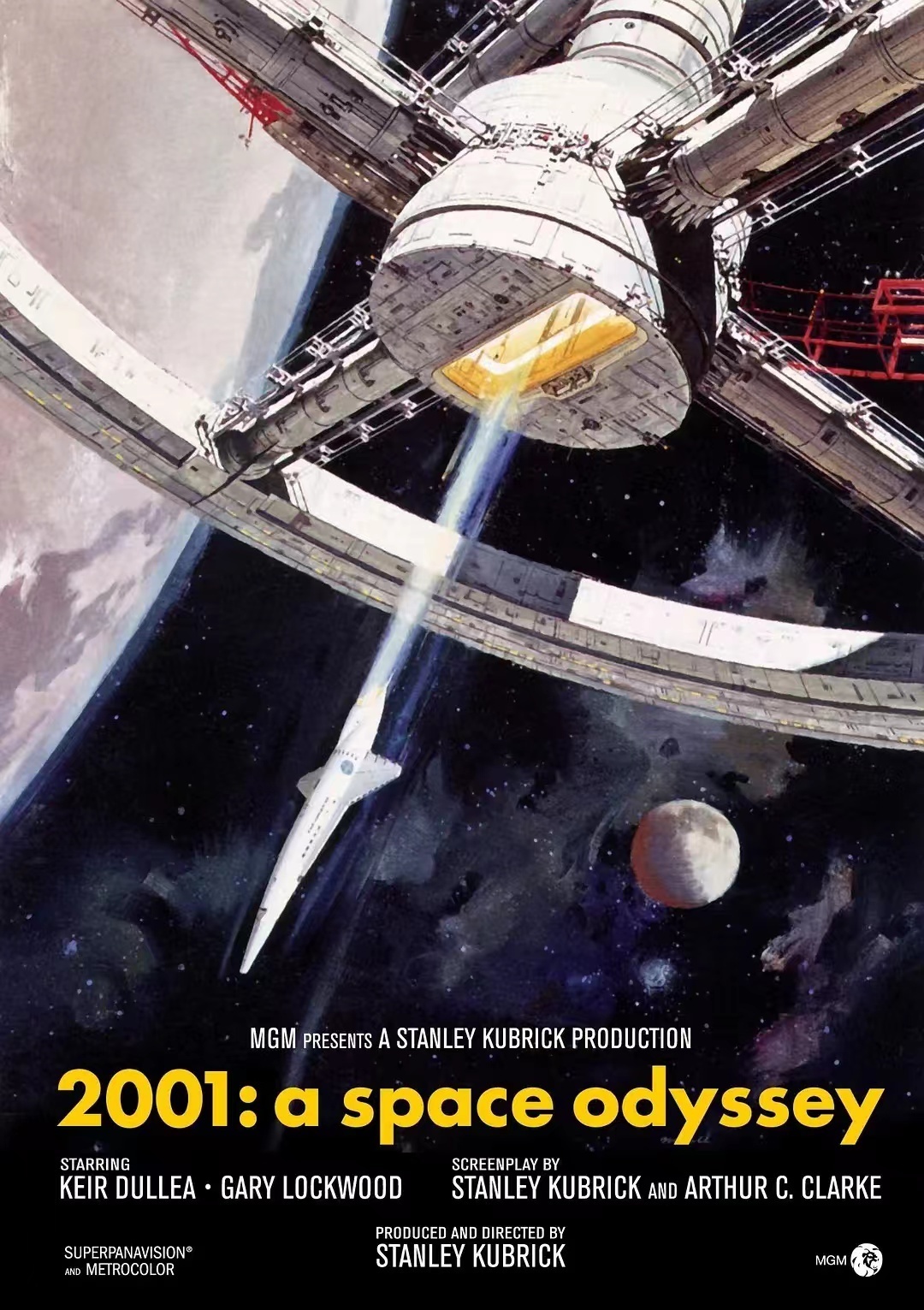
1968!1968!1968!(為1968年上映的好萊塢電影震驚而打的三組數字。)

我一直認為預算不是判斷電影品質的唯一標準,甚至不是主要標準。精美的畫面、恢弘的場景、明星導演+全明星演員不等於出色的電影,然而在宣傳電影時,這些元素卻是必不可少的。在今天,電影的定位實屬有些模糊。在它成為完全的商品或工業製品之前,曾經有一批卓越的電影人,尤其在新現實主義之後(安東尼奧尼、帕索里尼、費里尼、阿倫.雷乃、塔可夫斯基、伯格曼等人),將電影上升到現代藝術的范疇。這其中包含雙重含義,一方面是內在與外在現實實現了在銀幕上有機結合,如同喬伊斯、普魯斯特等人的文學,貝克特與漢德克的戲劇一樣,從古老的敘事目的中解放出來,煥發新生;另一方面,作為技術革命推動下誕生的「現代」的產物,電影攀升到了「藝術」的高度,一部部經典作品的產生意味著已被確定的過去的輝煌,這一歷史的包袱使得它在文化工業體系下難以判斷自身的位置,尤其相對於電視、短視頻來說,這些包袱顯得沉重冗雜。同時也使得被藝術電影遮蔽雙眼的人們忽視了電影的天然屬性:商品性。可以這樣說:電影是資本主義進程中的一個錯覺,當市場全盤接手電影時,輝煌便只能留在六七十年代的電影中被反復品味,或消費了。
《呼喊與細雨》是1972年的電影,伯格曼的作品。僅在一棟房子內,通過鏡語手法、極具張力的表演與蒙太奇組接,電影就形成了。某個定義是:電影是用視聽語言表意的藝術形式,它是用鏡頭說話的,而並非是依靠直抒胸臆的文字語言、音樂或對話拼湊而成的視覺成品。我們知道,電影是一個整體的概念(《俄羅斯方舟》或許是最直接的佐證,不過對電影作為整體的理解需要通過拼接的過程來實現),而在伯格曼們的語境中,這一整體意味著不斷地開放,即便它已經確定,也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生成新的內容。今天的電影總喜歡迫不及待地表達什麼,有些討喜(《芭比》),有些則略微聒噪(《黃金三角》),還有些則令人厭煩(自我感動的說教片),這些急迫的電影以另一種形態回到了早期的好萊塢電影中,只不過更善於裝飾了。伯格森①將糖放於水中等待融化時說道,我必須等糖化開,而不是藉助外力攪拌加速融化。我不是需要一個糖水的結果,我是需要的是等糖化開。這一過程,被稱為「綿延」。
戴錦華曾說自己有位數學家朋友選擇看伯格曼的電影放鬆自己,無思、無想、無慮,只是看,然後舒緩。這大概是對電影的最高評價。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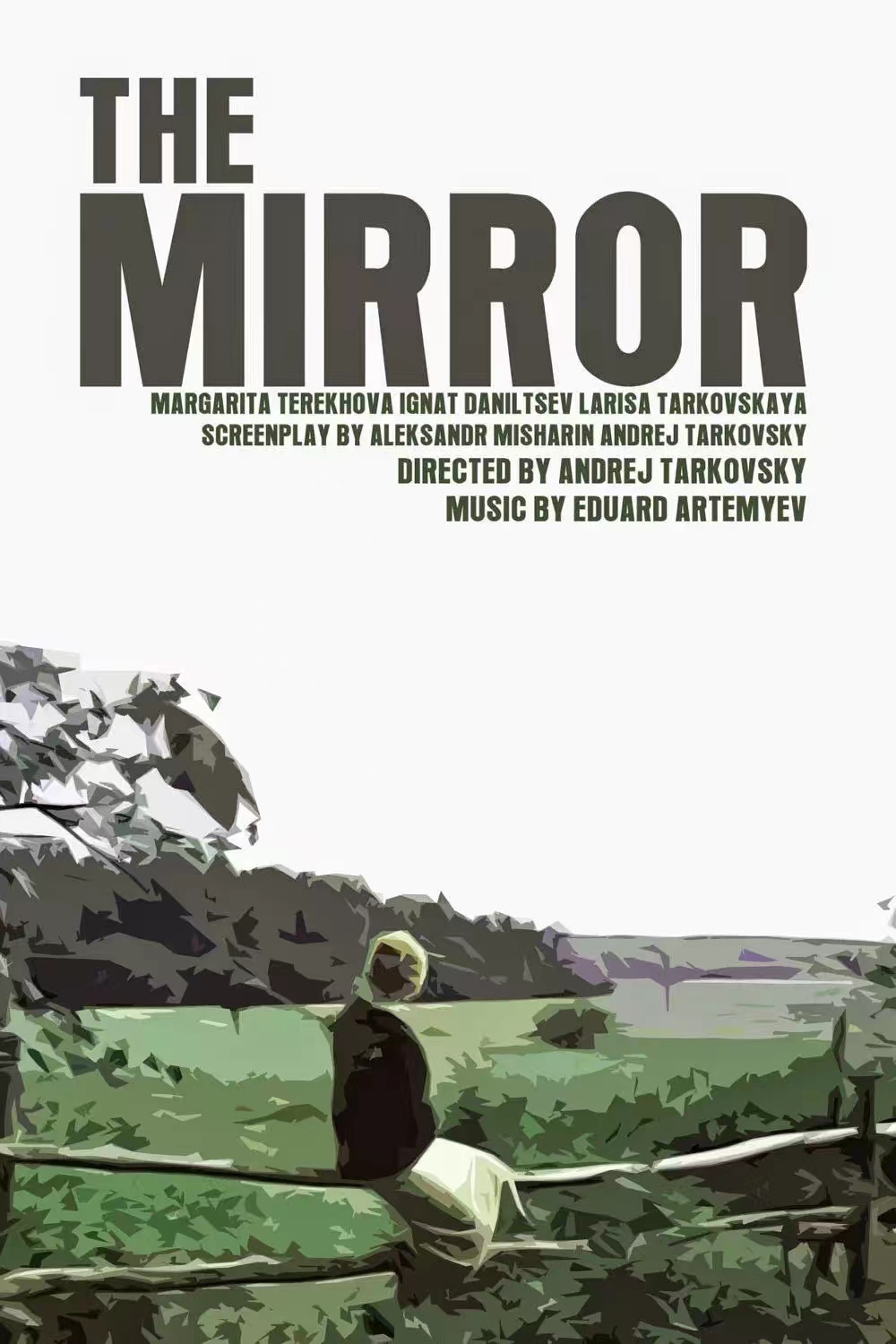
我沒看懂。
影像同附魔般牽著我的眼睛走。
我的眼睛好忙,一會兒要看畫面,一會兒又要看字幕,深怕什麼都丟了。
到最後,詩人再次誦讀時,我把字幕關了。我默認,這里聽不懂的語言是詩。文字的軀干。
然而,有一段影像極速將我與影片的距離拉近,剎那間,一切關於曲高和寡的臆想便從腦子里消失了,我知道那是什麼。
我知道西班牙內戰、核彈、大清洗;正如我知道契訶夫、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與變了裝的高爾基;正如我看見些卡拉瓦喬的影子,聽見些巴赫的曲調;正如我對東正教,或對斯拉夫民族的困境略知一二。
美啊,自然。濃郁的火與岸邊皚皚。
我希望在我三十二歲時,在冬天,暴雪過後,還能再看一遍。

正如那些新浪潮前輩一樣,亞歷克斯射出的子彈以極速的張力略過敘事的高潮,最終射入自己的體內。米歇爾①流露出最終的倦怠,亞歷克斯則將倦怠釋放出來。在這一張一翕中,實現了法國藝術電影傳統的反叛閉環。
多說一句,這部電影極為養眼。
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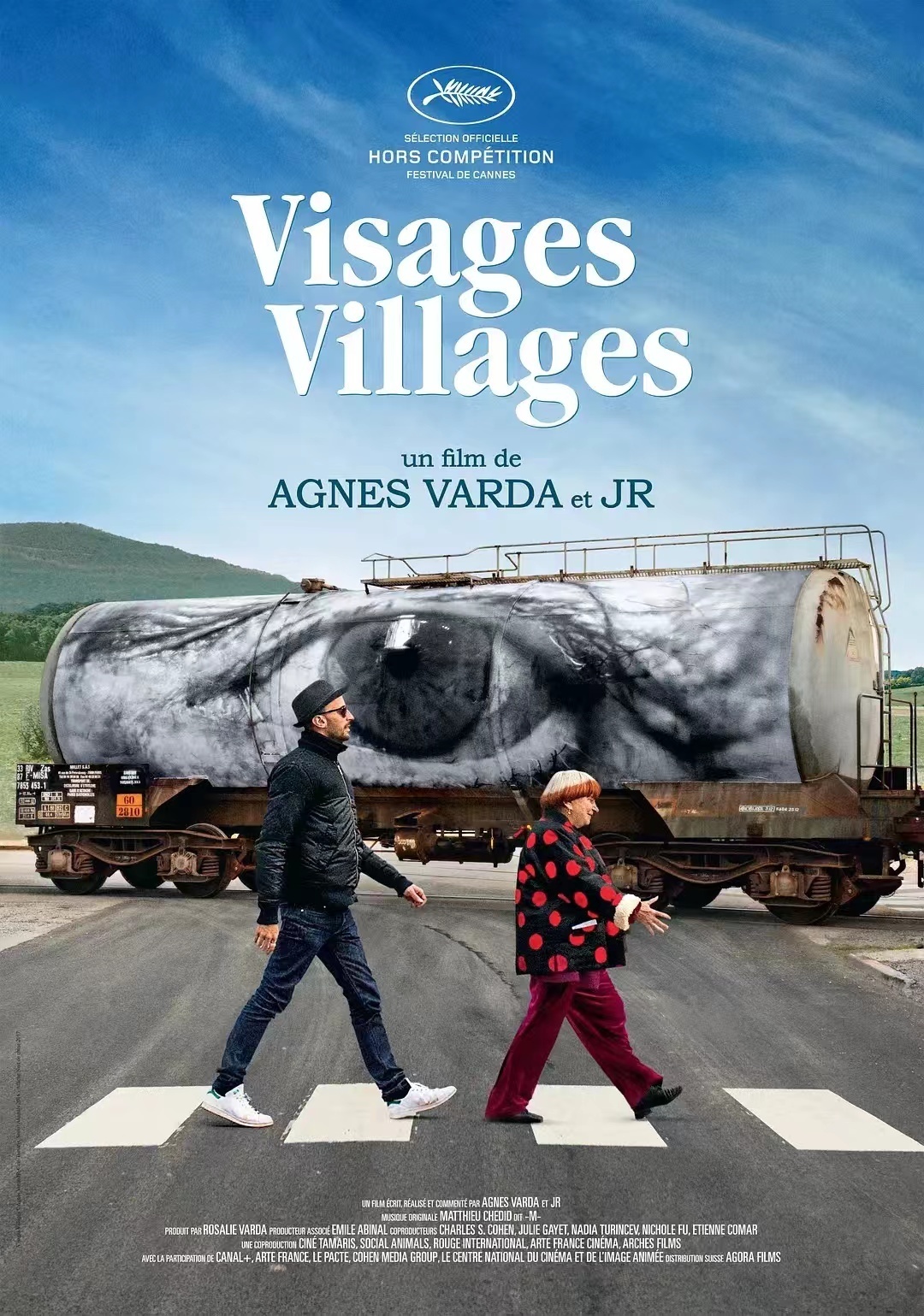
一舉扭轉我讀桑塔格《論攝影》後對攝影的不信任感,當然,也僅僅是瓦爾達與熱內輕快的影像記錄。我想,正是因為他們將相框內外一並兼容,才使得他們並不拘泥於相框的制約——臉龐本身就是美的,關鍵在於攝影人如何看待ta。當人們致力於把相框內的臉趨於同一審美甚至完美時,記錄本身就成為了例行公事,讓本身輕盈之事變得沉重,是今天我們常做的事。
不過戈達爾確實挺混蛋的(揮拳)。

當然,一部好電影往往有無數種解讀的方式,但無數種中只有少數與電影本身有關。例如女性觀眾能與女主共情,男性觀眾同情死者,當性別成為我們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時,狹隘是不分道德高低的。巧妙的是,《墜落》通過鏡頭正是展現這種偏狹帶來的對於真相的歪曲。我們的世界被影像包圍,被照片裹挾,所能看見之物愈發繁雜,卻離真相越來越遠。看見的太多,所以想像的單調,而什麼都看不見的,反而能接近真相。顯微鏡下的每一個人、事、思想都經不起推敲。世界是由亂麻編織而成的,對錯之分能剪斷其中一根,於是我們一口咬定那截面便是全部,因為這樣最快、最高效。
PS:可在3月29日去電影院觀看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