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按
最近我正在總結自己關於控制論的認識,發現線索總是回到梅西會議,這個著名的跨學科研討會。會議時間雖然略顯久遠,而且多數報告如果不具備相關領域知識,也極為難懂,但會議內容卻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於是我就順便翻譯了1953年會議主席沃倫·麥卡洛克在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梅西會議上所做的總結,當作會議的一個簡略到不能再簡略的框架。
這份材料在第十次控制論會議之前分發給了參會者。這是一篇幾乎不能被稱作總結的總結,因為它算不上主題明確或邏輯緊密,而更像是不得不將參會者們的各種觀點按照一個敘述線索串聯形成的講稿。雖然參會者一致同意將後五次會議更名為「控制論:生物和社會系統中的循環因果和反饋機制」,但很難說會議形成了某種知識層面的共識,麥卡洛克這樣說道:「我們所達成最顯著的一致意見就是,我們學會更好的瞭解對方,並且身著襯衫公平的彼此爭鬥。」
這與梅西會議的跨學科性質和會議議程安排密切相關,麥卡洛克在他劃定的每個學科中都至少邀請了兩名學者,為了他們可以彼此印證。而且討論時的每一個話題,都會經歷雙重討論(dual treatment),基本上是來自硬科學和軟科學的科學家相互類比和討論,期間發生了非常多激烈的爭吵。將這樣的會議過程整理為邏輯連續而且看起來比較體面的文本,難度可想而知。這種觀點激烈交鋒而略顯混亂的狀態,被麥卡洛克謙虛地稱為「嚴重無知,甚至理論無能」。
不過麥卡洛克並非在責備或惱怒,他只是坦率地承認尚未找到一個完備的坐標系,能完全統合這些各個學科當時最前沿的發現成果(或許再也不需要了)。這些來自生理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物理學、語言學等完全不同領域的觀點經常在同一議題下不可思議的並列出現,甚至有時相互矛盾。但不可否認的是,其中的諸多觀點的報告來源,或許都是各自領域中有關鍵性啟發的文本。
也正因如此,由於個人知識儲備所限,譯文可能無法准確轉譯所有術語。如有相關專業的朋友,請予以指正。或有瞭解相關研究後續發展的朋友,還希望能一同討論。
沃倫·S·麥卡洛克 Warren S. McCullo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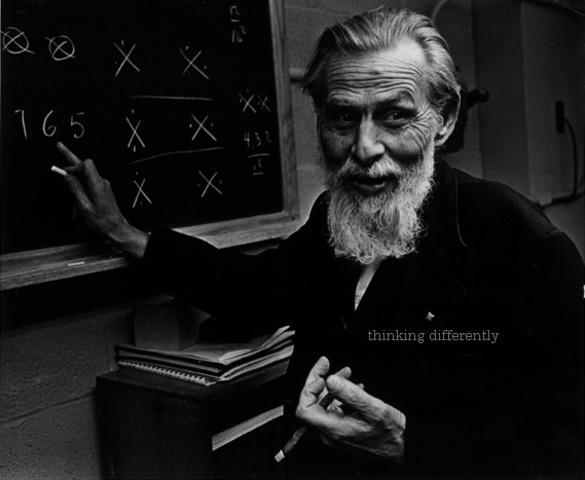
1898年11月16日-1969年9月24日,美國神經生理學家、控制論學者。他與沃爾特·皮茨合作的一系列研究將人類的神經活動數位化、邏輯化,為神經網絡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其中以1943年的《《神經活動觀點下的邏輯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in the Ideas of Nervous Activity)和1947年的《我們如何知道共相對聽覺和視覺形式的感知》(How We Know Universals The Perception of Auditory and Visual Forms)兩篇論文最為著名。麥卡洛克還擔任了梅西會議主席,梅西會議跨學科的多樣性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的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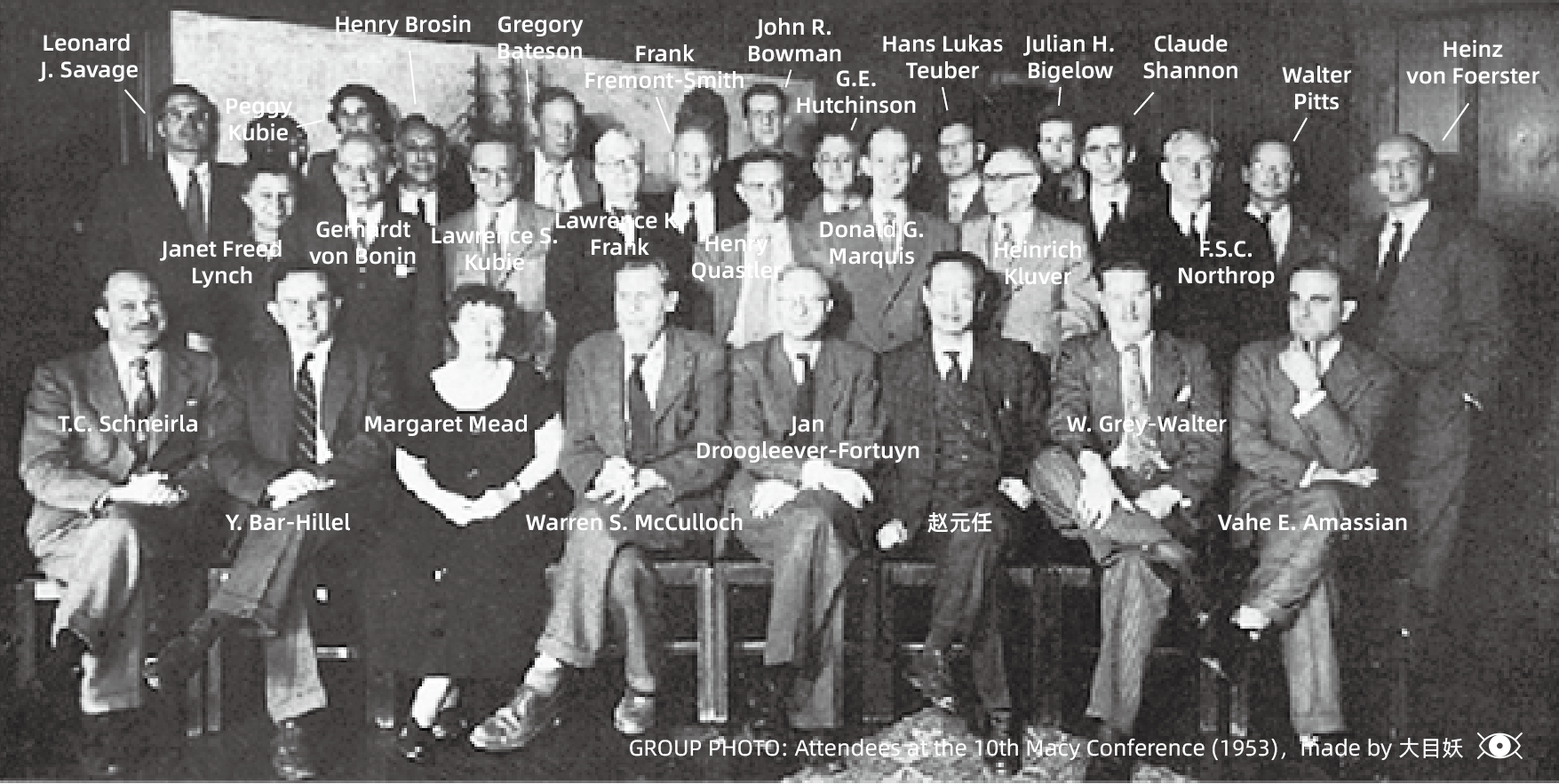
Summary of the Points of Agreement Reached in the Previous Nine Conferences on Cybernetics
前九次控制論會議達成的協議要點總結
沃倫·S·麥卡洛克
Research Laboratory of Electronic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ss.
愛因斯坦曾經把真理定義為,通過考慮觀察結果、它們的關系和觀察者的關系而獲得的共識。在他的例子中,觀察結果是參照系中各個點的信號的重合;它們的關系是這些參照系中的空間和時間問題;愛因斯坦的觀察者被簡化為亥姆霍茲(Helmholtz)所說的觀察點(a locus observandi),缺少偏見與想像;他必須考慮的唯一關系是它們的相對位置、運動和加速度。愛因斯坦心目中的真理是一幅所有觀察者都能認同的世界圖景,因為它的表達採用了一種不變的方式,隱含在表示觀察者關系所需的變換之下。它是一個關於「科學認同」(scientific agreement)可能意味著什麼的範式。
而對我們(梅西會議參會者)來說不幸的是,我們的數據不可能被如此簡單地定義。它是通過極其不同的方法收集的,來自多元稟賦和培訓的觀察者的不同傾向,並且只通過實驗室俚語和技術術語構建的脆弱巴別塔相互聯系。我們所達成最顯著的一致意見就是,我們已經學會更好地瞭解對方,並身著襯衫公平的彼此爭鬥。這聽起來很民主,或者往好了說,是無政府主義,正如你們兩次提醒我的一樣。
除了理論上的同義反復,以及通過個人觀察問題事實而獲得的特別權威,我們的意見從未一致過。即使是這樣,我也看不出上帝有什麼理由會同意我們。因為我們一直雄心勃勃地尋求那些概念,它們超越所有目的性行為和對我們世界的所有理解我指的是目的論的機械論基礎,以及信息在機器和人之間的流動。在我們自己的眼里,我們被判定為嚴重無知,甚至理論上的無能。
我們的會議之所以開始,主要是因為諾伯特·維納和他在數學、通信工程和生理學方面的友人,已經表明逆反饋(inverse feedback)的概念適用於從蒸汽機到人類社會的所有調節、穩態平衡(homeostasis)和目標導向的活動問題。我們早期的會議主要致力於使這些概念在我們的頭腦中變得清晰,並發現如何在不同的領域中使用它們。
在會議間隙,我們中的許多人在這些概念的啟發下進行了觀察和實驗,但我們普遍發現在兩次會議之間的6個月內很難收集到足夠合適的數據。因此在前五期會議結束時,我們選擇之後每年只舉辦一次會議,以盡可能地保持核心小組的聯系,替換一些離我們而去的人,並邀請一些演講者在我們最需要的地方予以幫助。(譯註梅西會議參會者由核心小組和嘉賓兩部分組成,核心小組大致等於常駐成員,每次會議會進行人員的調整。)
當做出這一調整時,我們已經發現,在任何伺服系統(servo system)的所有負反饋(negative feedback)問題中,至關重要的不是返回的能量,而是有關迄今為止的行動結果的信息。我們的主題慢慢地、不可避免地轉移到仍然由諾伯特·維納和他的朋友們主持的領域。很明顯,每個信號都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物理的,另一個是精神的、形式的或邏輯的。這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了計算機器(computing machinery),轉向了作為負熵的信息存儲。這屬於編碼、語言及其結構、如何學習以及如何理解的問題,包括這最後一次會議的主題。本次會議上,我們期望涵蓋從語義學的最正式的方面,到它與我們週遭世界最豐富的接觸。為了我們所有人,我希望維納仍然和我們在一起,但我知道他目前正愉快地沉浸在相對論清晰而寧靜的領域之中。(譯註:維納在第七次會議後退出了梅西會議。最後一次會議為第十次會議,議題為:1.大腦活性的研究;2.語義的信息量及其度量;3.語言的意義及其獲得方式;4.神經機制是如何識別形狀和音樂和弦的;5.梅西會議達成了怎樣的共識?如果存在的話。)
為了喚起我們的記憶,並告知各位嘉賓,讓我按照邏輯而非時間順序,重述我們所審議的議題。在這些議題上,雖然受到我們理解證據或理論的能力的限制,但我相信我們大多數人都能達成一致。相比與我們發表的匯刊,你們可能在我的發言中更多地發現共識。我迫使自己觀察你們的表情,並在我讓你們發言之前,猜測你們是否會就這個問題發言,以及站在哪種立場。我懷著惡意讓不滿的人發言,因為他不同意或者懷疑,無論這有多麼不合理。在我這麼瞭解你們之前,這只是偶然發生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學會了彼此的語言,我明白這是保持我們機警的最好方法。我們的嘉賓都很有風度,但我們討論的記錄有時不可避免地導致誤解和爭吵,而非達成一致。而那些理解和同意這些記錄的人,則不會留下一絲痕跡。
反饋(feedback)被定義為通過輸出改變輸入;增益(gain)被定義為輸出與輸入之比;如果返回(return)減少了輸出,例如從輸入中減去,則反饋被稱為負反饋(negative)或逆反饋(inverse)。同樣的術語,逆反饋或負反饋,被用於效果類似但不同的機制,其中返回減少了增益。信號的傳輸需要時間,而增益取決於頻率;因此,對某些頻率而言逆向的電路,對其他頻率則可能是再生制動的(regenerative,有放大、正反饋的意思)。當增益超過1時,所有的電路都成為了再生制動的。再生制動傾向於極限偏差(extreme deviation)或裂生振盪(schizogenic oscillation),除非增益隨著信號振幅的增加而減少。
逆反饋決定了系統要尋求的某種狀態,因為它使系統返回到該狀態,而逆反饋的量會隨著系統偏離該狀態而增加。伺服機構(servomechanisms)是這樣一種設備,其中的系統要尋求的狀態是由從其他來源發送到該系統的信號所決定的。這些概念被應用於機器,包括蒸汽機及其調速器、船舶轉向舵機、穩壓電源組、電話中繼器、自調式收音機、自動火炮瞄準器等,此後又被應用於生命系統。
穩態平衡(homeostasis)最初是在反射機制方面被考量的,在這種機制中,身體某部分產生的變化引起了擾動,例如神經沖動,這些沖動最終被反射到產生變化的身體部分,並在那里停止或逆轉了引起這些沖動的過程。完全處於中樞神經系統內部的類似的調節迴路,也能在商業收音機的自動音量控制中找到相似的迴路。
欲求行為被描述為一個環路(loop)的逆反饋,其中一部分在有機體內,一部分在環境中。當能夠指出一個目標或目的時,人們發現對欲求行為的描述與自控魚雷和自我訓練火炮的描述相同,無論這些設備發射的信號被其目標反射,還是僅僅依靠目標發射的信號來重新調整隨後的行為,以適應先前行為的結果從而使其誤差最小。
維納在小腦與炮塔、現代絞車和起重機的控制裝置之間做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比較。在每種情況下,小腦和這些機器的控制裝置的功能都是預先計算伺服機構所需的指令,並使已經開始運動的物體在預先指定的位置上靜止,否則由於慣性的原因,它將會達不到目標或過頭。這些概念為後來的神經生理學研究提供了指導,這些研究涉及控制位置和運動的神經系統的功能組織。其中有些實驗是在我芝加哥的實驗室進行的,有些是由維納、皮茨和羅森布魯斯在墨西哥城的心髒病研究中心進行的,還有我們在其他實驗室的朋友進行的。
我們發現一般的組織是由多個閉合的控制迴路組成的,但迴路的作用是極其非線性的,因此無法用傅立葉理論進行任何一般的簡單數學分析。一般來說,多個環路(loop)能通過逆反饋各自穩定,而聯結在一起時可能不穩定,但系統可以通過將每個返回的一部分相加並減去一個或多個伺服的總和而使其穩定。這種系統先由謝切諾夫(Setchenow,俄國生理學家、心理學家)於1865年在中樞神經系統中發現,並隨後由賀拉斯·馬古恩(Horace Magoun,美國神經生理學家)再次發現。我們的一個小組正在研究該系統的多種傳入的細節和它影響所有反射活動的方式;我們將使用破壞性的病變,並將用上次會議中提出的方法刺激並繪制神經系統各部分的源和匯(sources and sinks)。隨著抑制性信號的失效或增益的增加,牽張反射變得再生制動(譯註:牽張反射,stretch reflex,又稱為深反射、腱反射,可被看作為一種刺激肌腱、骨膜的本體感受器所引起的肌肉快速收縮反應),產生音調的上升和一系列的矛盾,被稱為陣攣(clonus)。羅森布魯斯、皮茨和維納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優雅的定量分析,正如在會議上所述。此外,他們還能夠證明,所謂的單突觸中繼池(the pool of relays of the so-called monosynaptic)顯示出兩組數量眾多,和第三組數量較少的中繼群,這是由三個最大值周圍的閾值的隨機分佈所判斷的。我們還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全運用這些概念。
中樞神經系統內的閉合環路——首先由庫別(Lawrence Kubie,美國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家)提出,作為行為主義者提出的不可探索的運動活動的替代品,以解釋反射方面的想法;然後由蘭森(Stephen Walter Ranson,美國神經生理學家、解剖學家)提出,以說明中樞神經系統內的穩態平衡過程;之後拉斐爾·洛倫特·德諾醫生(Rafael Lorente de Nó,西班牙神經解剖-生理學家)獨立發現並證明了眼球震顫的情況——這被麥卡洛克和皮茨提到可能用來解釋短暫記憶,並且表示這作為對所有形式記憶的解釋,在邏輯上是充分的,但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利文斯頓(William. K. Livingston,美國神經學家)提出,這種機制可以解釋阻斷或切除變態外周迴路後的灼痛症狀,這些外周迴路因某些創傷而顯現出再生制動,導致小傳入神經元(small afferent neurons)上的沖動流將灼痛當作獎賞。庫別提出,每一種神經症的核心都是某個閉合環路中的一種反復過程。
我已經總結並向英國皇家醫學會提交了所有這些方面的證據,以及從灼痛的多種干預中獲得的更多證據。很明顯,「反饋」是理解有關結構的正常功能和疾病的適當概念。從那時起,里昂的加拉瓦丁醫生(Louis Gallavardin,法國醫生、心髒病學專家)在研究伴有口、舌和喉部肌肉活動的幻聽患者時,曾雙側切除了面部的中樞後體感區。當我最近一次聽到他的消息時,患者隨後的幻覺已經消失了18個月。這使一種明顯的器質性精神病的症狀與對那些至少暫時得到額葉切除術幫助的強迫症患者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即大腦內某些回響(reverberative)過程的中心通路已被部分打斷了。
同樣根據這些概念,我們已經能從心理學家聲稱的目標導向活動(goal-directed activity)的某些方面看出端倪。我們注意到了前進和逃跑的不對稱性,因為在前者中,所尋求的對象被保持在感覺器官接受領域的中心附近,並且行為被適當地修正以接近對象;而在逃跑中,沿著這些路線學習是不可能的,而且行為可能很容易變得刻板。我們所聽到的最復雜的情況,是主要由社會人類學家報告的與世隔絕社區的社會結構中的逆反饋所產生的穩定性。他們的方法非常復雜,在某些情況下,取決於許多交織在一起的環路。他們似乎在親屬關系、稱呼方式、欺凌、贊美、指責,甚至在飲食儀式等方面使用了形式繁復的區分和規則。來自生態學和蟻穴行為的例子擴展了這些逆反饋的概念。
我們對經濟學和民意調查感興趣的成員利用這些概念來解釋市場的波動、導致公雞和男孩打架的戲謔,以及引發戰爭的軍備競賽。在這樣的循環系統(circular system)中,識別因果關系變得很困難。維納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指出,在相關組合事件的時間序列之間的相關性並不完美的情況下,有可能通過延遲的自相關和互相關性來識別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並解釋了如何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最佳預測。他懷疑這種方法對社會問題的適用性,因為人類行為中時間序列信息的運行時間很短。在這些方面,我們討論了一名外野手如何接球,以及一隻貓如何抓老鼠。
然後,精神病學家提出了動機之間的衝突問題,他們和心理學家一樣,希望在人類欲望之中找到一些共同的價值衡量標準,這與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在自由市場的邊際效用和價格學說中所發現的相類似。庫別提出了不同目的的緊迫性問題,從對適宜溫度、空氣、飲料、食物、睡眠和性的需要開始,最緊迫的需求導致最簡單的反應,而最不緊迫的需求則允許精心設計的玩耍。
我指出,一個擁有六個神經元的生物體,構成了三條逆反饋鏈,並通過疊加或抑制性連結相互關聯,其復雜程度足以顯示出價值異常,而且如果將組織配置交給偶然性,那麼一半的時間都會如此。也就是說:給定A和B,它更喜歡A;給定B和C,它更喜歡B;但給定C和A,它卻更喜歡C。一個類似的問題是關於雞的啄食順序中的支配地位,但對於給定數量的雞籠中的循環,並沒有足夠的數據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時,我們已經對反饋概念的廣泛延用感到厭煩了,所以我們同意在餘下的會議中嘗試放棄這個話題。
在這一點上出現了兩個有趣的離題:第一個是關於心髒顫動,它表現為在一個其無法越過的區域的外圍遊走的傳播性干擾,因此它無法使自己停止,然而心房顫動則表現為一種干擾,即在不斷變化的路徑上徘徊,這些路徑由先前在這些點上的活動產生的閾值變換所決定。現已對其進行了數學分析,但未提交給小組。第二,皮茨提出了一個關於隨機網(random nets,例如大腦皮層)中的干擾的理論,在該理論中有可能找到一個擾亂活動的數值;即一個神經元中的信號的機率等於與傳入它的神經元中的信號的機率。
此外,我們都已經認識到,對於反饋問題,考慮能量問題是錯誤的。其中關鍵的變量顯然是信息。
我們最初認為,如果電壓、壓力或長度等連續變量的大小與輸入計算的數字成比例,計算機就是「模擬的」(analogue);而如果它們是被不穩定區域隔開的一組穩定值(至少兩個),並且數字由一個或多個組件的穩定狀態的配置所表示,則是「數字的」(digital)。模擬設備顯示,錯誤傾向於出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但受到製造精度的限制,無法通過相互組合來保全更多的位置。數字設備可能會在任何地方出現錯誤(這是所有位置命名法中固有的缺陷),但不需要極高的精度,而且總是可以通過相互組合來保全另一個位置,每個位置的價(price)都與先前相同。當組件為繼電器時,數字設備在每次重復時都會銳化信號。
我們考慮將圖靈的通用機作為大腦的「模型」,並使用了皮茨和麥卡洛克對神經網絡活動的邏輯算法——它採用了《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羅素與懷特海合著)中的命題演算,下標出某一給定神經元脈沖的發生時間。我們證明了所有通用圖靈機的等價性,以及如何設計它們來回答任何能夠以明確方式提出的非矛盾問題。我們考慮了從哥德爾(Kurt Gödel,美籍奧地利數學家、哲學家)的算術邏輯中得出的被廣泛延用的結論。很明顯,產生想法(having ideas)需要電路能在必要的變換組下計算不變的量,也就是說,反射活動保留了它傳入的形式,同時啟動,或者逆反饋使一些輸入的數字通過某些路徑導向其諸多合理呈現中的規范典型。
格式塔的概念僅僅導致了歸因於「皮層場」的細節的扭曲倍增,雖然在自然中有其源和匯,且它們遍布的皮層區域在解剖學上是不連續的,但其中電流是守恆的。神經組件的離散動作被認為是它們能夠正常運作以處理通過它們傳輸的大量信息的唯一方式。嚴重的功能障礙(癲癇等)被認為伴隨著過度的波動,以幾乎相同的方式影響特定區域內的大多數神經元,從而產生信息的損失。情緒被認為是計算機某些部分溢出的表現,對擴散性和可變的輸入產生某種固定的反應,就像在圖靈機中一個運算對象(operand)的計算值不再影響後續的操作。
維納提出,情緒可能會通過腺體方式(glandular means)廣播一個「致相關者」的信息,導致項目被鎖定或被記住。有人建議,找出一個未知機器能做什麼的最佳方法,是給它提供一個隨機的輸入;毫無疑問輸入必須是隨機的,以便機器可以分辨輸入的各個方面。這好比羅夏測試,以及其聽覺等效測試,並且有人指出,自由聯想產生的胡言亂語很容易導致精神病醫生將自己的困難投射到病人身上。
會議詳細討論了三種稱為記憶的儲存。第一種類型的儲存,例如聲學試驗水槽中的主動混響(active reverberation),被認為是眼球震顫的原因和老年性精神障礙的唯一儲存。約翰·扎卡里·楊(John Zachary Young,英國生物學家、神經生理學家)使用同樣的概念來描述章魚的主要記憶器官被破壞後的殘留記憶。
第二種類型的存儲,只發現在章魚之中,它占據了一個獨立的結構,有明確、獨立的出入信道。該器官本身由許多小細胞組成;其突觸的性質尚不清楚。這是一個令理論物理學家感到興奮的存儲,因為它所保留了數量巨大的比特。馮·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美籍奧地利物理學家,哲學家)根據接入時間乘以接入信道與痕跡的平均半衰期來計算其大小,而斯特勞德(John Stroud,美國心理學家)則根據每十分之一秒的快照數量來計算,例如,每幀一千比特。數字大致一致,位於10的13次方和10的15方之間。有百分之幾的項目被永遠保留,而非逐漸地降至零。
馮·福斯特提出瞭解釋這種現象的機制,大約需要0.02瓦特;而大腦是一個24瓦特的器官。對該種存儲的訪問可能不是通過簡單的串行地址尋找。回憶似乎是建立在一個通過內容定位項目的過程之上。馮·諾依曼討論了相似的問題,克魯弗(Heinrich Klüver,德裔美國心理學家、神經學家)討論了刺激的等價性問題,但兩人顯然都注意到了清晰記憶片段的保留問題,這個問題應該在下文中更深入地討論。人類的這種存儲的特點似乎是內容是一系列的快照,其中每一個都不會移動;它們可以按照歸檔的順序訪問,而非相反;在造成記憶痕跡和它第一次被訪問之間有大約一分鍾的延遲;最後,一個與之前的快照過於相似的快照可能會破壞這個過程。這些痕跡不能被簡單地定位;每個比特都是網絡中某個地方有效突觸的變化,而且這種改變並不侷限於某一個結合點。
第三種類型的存儲似乎更像肌肉隨著使用而增長的特性,並且在過於頻繁的測試中顯示出疲勞。舒拉格(Phil Sheridan Shurrager,美國心理學家、教育家,運動神經元突觸脊柱調節與學習的提出者)顯然有證據表明,它可以發生在單突觸反射層面上,在迷走神經與青蛙耳廓的神經節細胞接觸的地方,已經看到了隨使用而發生的變化,但沒有證據表明這種變化在中樞神經系統的任何地方持續存在,也沒有解剖學證據表明它曾在那里發生。也許正如艾什比(Ross Ashby,英國精神病學家、神經生理學家)所提出的那樣,在使用過程中確實發生了一些組織的變化。視覺皮層的組織隨使用而變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先天性白內障被切除後,人們發現視力困難部分是由於中樞神經系統其它部位的脈沖對這些機制進行了相反的配置組織。
大腦的「交通堵塞」的可能性隨著容量的增加越來越大,因為除非通過不成比例地增加纜線空間(cable-space),否則長距離連接的數量無法與要連接的繼電器數量同步增加。有人提出,勞埃德(Lloyd)所描述的增效(potentiation)可能有助於在先前使用的基礎上暫時鎖定線路;這類似於荷蘭提出的更有效地利用有限電話設施的方案。因此,當軸突被超極化時(P2後電位,hyperpolarized,譯註:超極化指神經細胞膜的一種生理狀態,可使神經元處於暫時的抑制狀態。),離開細胞體和樹突的腦脊髓神經元重復發射。這解釋了以大腦皮層表面負極和深度正極為標志的增強組件,伴隨著傳輸到脊髓電壓的增加而產生的降低閾值的問題。同樣的機制也可以解釋帕金森病人的僵直現象。
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來討論信息實際流量決定群組結構的方式,並討論指令每時每刻的移動方式:即移到網絡中的行動所需的大部分信息集中的某個地方。在包括大腦在內的並行計算機器中,當一個部分繁忙或損壞時,另一個部分將用於相同的計算。這就要求整台機器由機器的某個部分接管,該部分能夠將問題切換到自己身上。這種機器可能會在大部分機器失靈的情況下給出正確的答案。這一方面看起來是神經元和由它們組成的通道的冗餘問題,另一方面則是確保從易錯的部件中獲取可靠執行的問題。馮·諾伊曼關於該問題的最後一項工作,發表於西海岸的一次會議上,題目為《機率邏輯》(Probabilistic Logic)。
關於語言,作為僅次於視覺的大腦信息來源,二者在人類交流中都很重要,更不用說在精神分析之中了。人們普遍認同,除非我們希望別人做些什麼,否則我們幾乎從不說話。除了這種普遍的祈使性之外,語言還包含一些符號,例如「哼」(hmm)、「嗯哼」(um hum)、「啊……嗯……」(unh unh )和 「呵呵」(huh),這些符號很特別,但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內容。問題是,邏輯助詞(logical particle)是否來自於狗和小孩子使用的符號。人們普遍認為,正如米德博士(Margret Mead,美國人類學家)所言,當所有的定義都必須是指稱時(ostensive),比如在學習一種不存在翻譯可能性的語言時(作為一個孩子,或者一個新來到說外來語島嶼的人),最好是向兒童學習,因為他們會無限地重復。學習首先被定義為一種轉換機率的改變。語音,被分解成音素,根據雅克布森(Jakobson)的說法,由對立面之間的幾個判斷來區分,在英語的傳統拼寫中表現很差。用利克立德(J.C.R.Licklider,美國心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的方法,將語言切割和扭曲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來研究,除了當氣壓波動穿過軸線時的指示外幾乎留不下任何東西,甚至就保持其可理解性來說,這也是相當冗餘的。
在這一點回到每秒十張快照的問題上,當每十分之一秒中有一半是語音另一半是高出很多分貝的噪音時,語音仍能保持其可理解性的特性。語音所傳達的信息總量可能不超過每秒十比特,盡管每秒需要一千比特才能產生一個難以與其區分的聲音。香農在減少英語中每個符號所傳達的信息量冗餘方面的研究工作,是基於他與維納共同的看法,即信息是負熵(譯註:實際上後來香農的看法與維納相反,香農認為信息與熵是對等的,而非負熵,這部分由於香農將自己的研究明確限制在純技術領域,而非向維納一樣將信息/負熵與更宏大的組織度量和社會相聯系)。接收者有一組對象來匹配他所要接收的信號,而信號使他做出選擇。這種選擇性信息被發現與麥凱(Donald M. MacKay,美國物理學家,神經生理學家)的登入信息(logon information)相當,但與他的密特隆信息(metron information,密特隆,信息計量單位)不同,問題在於一個密特隆信息的熵成本隨著密特隆數量的平方而增長,而非隨著數字上升。
我們考慮了齊普夫定律:任何給定稀缺性的種類數量都與稀缺性的平方成正比;但我認為我們對該定律的有效性、異常情況的基礎或它所預設的領域都不滿意。最後,我們提議研究我們的基因賦予我們的信息量,並盡力為我們自己理順那些由於話語層次混亂而產生的困難。我希望,在本次會議結束時,我們將同意非常謹慎地使用「信息量」(quantity of information)和「負熵」(negentropy)這兩個術語。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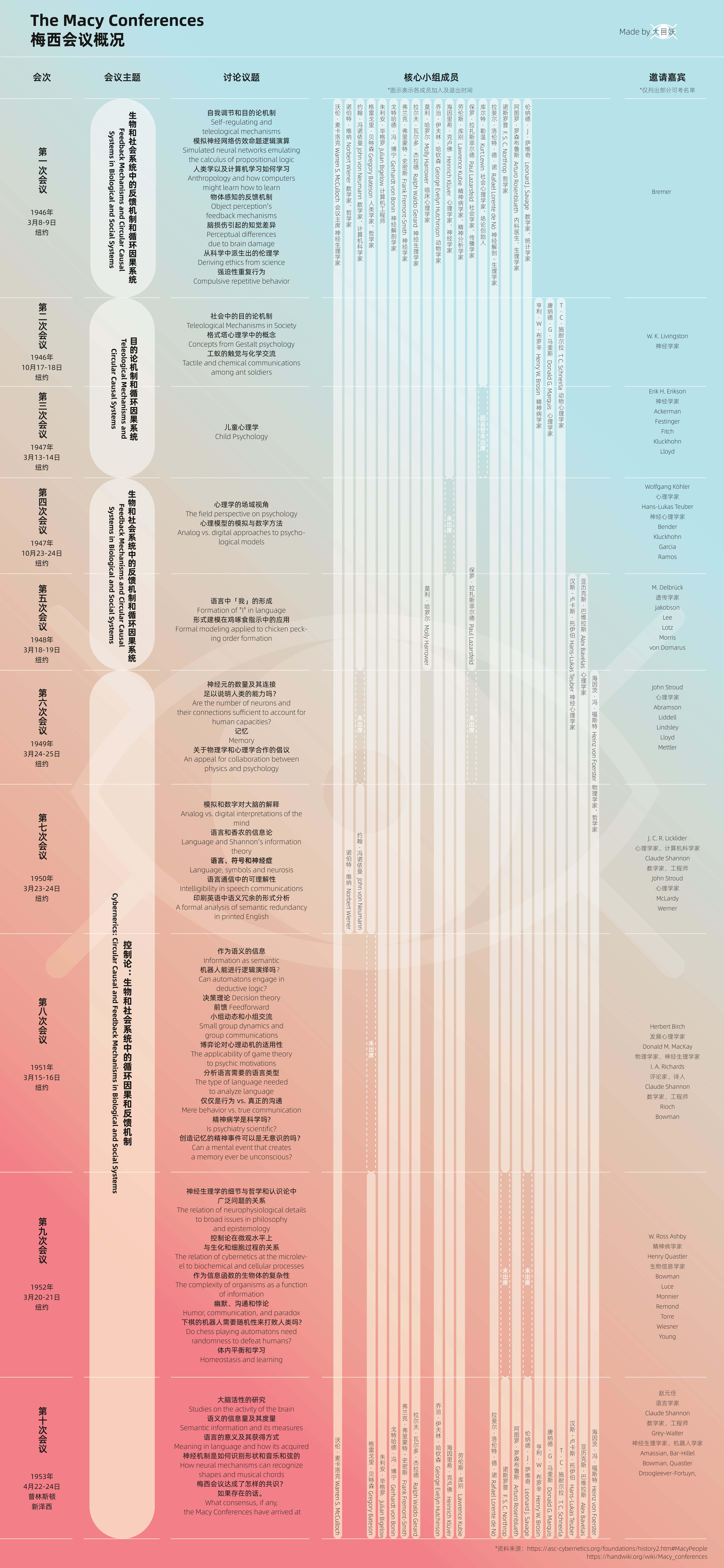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