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間連結:Oscar Barda 我花了十六年找到了對遊戲的定義(2016)
譯者按
這篇文章是我在網上偶然遇見的,充滿著對思索遊戲同路人的好奇翻譯了這篇文章,並且十分驚喜地發現他或許用較為簡明和清晰的方式(至少遠遠比 David Kanaga 的《筆記》,或者是 Ian Bogost 《電子遊戲是一團亂》 要易讀)闡明了某些遊戲的重要之物。這或許他在猛扎入遊戲研究後又能脫身而保持合適距離的緣故。
正如他所談的,去為遊戲/玩尋找定義是一件「非常危險」甚至「瀕臨毀滅」的事就正如1933年赫伊津哈在萊頓演講中警告的那樣「遊戲是一個吞噬一切的范疇,就像愚行(當愚行占據了伊拉斯謨的思想之後)已成了整個世界的女皇時一樣」。而我自己,與曾經陷入其中的同路人也曾親身感受過那種思考的危險。
所以當我看到這篇文章時我很開心,不僅是遇上了思索的同路者,也不僅是因為我像他一樣也如此熱愛《浪客行》。重要的是,我認為他給出的定義 fiction of doing,以及 formalized fiction of doing 的說法是有益的選擇。
對我來說,在接受了德勒茲對概念和哲學的看法後對於「何為遊戲」的回答尋找正確答案不再是我目的,重點在於發明一個怎樣的概念能夠揭示更多現實的晦暗(並非發明更多晦暗),即,概念能展開怎樣的思的速度與空間。
非常巧合的是,他思索遊戲的開端與我很接近「相信卻也不信(believes without believing)」,不過這在他視作開單子赫伊津哈「嚴肅性」,以及凱魯瓦「假信 make-believe」那里已有類似的傳統,此外他對體育的描述和概括稍顯單薄,而或許遊戲研究開始的時間可以上溯至康德會更合適些(遊戲嚴肅的譜系學與「假信」也是我最早的出發點,可參考拙文《「嚴肅」的遊戲》與《遊戲的高度嚴肅性》)。
但這或許都不是關鍵,我覺得他最終尋得的、我翻譯為「做的虛構」的概念比起其他復雜的,確實是有力、美、且有聯結的潛能的。例如在這點上我覺得能以此連通策展人漢斯·烏利齊·奧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所發起的一系列 do it 做了它的 DIY 藝術運動,以及更多包括引導的身體劇場,甚至冥想活動等。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 doing 就像他描述的,不只是行動(action),還有反思,感受,以及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指向一段展開的過程,就像他結尾所說的
遊戲是讓人做的藝術(art of making people do)
*封面為日本書法家井上有一的作品《花》系列之一
Oscar Barda

來自法國巴黎的遊戲設計師,遊戲設計理論研究者,創意總監。他的工作室叫做 themgames ,此外有一篇 GodArt 對他的有趣采訪,你可以在推特(Twitter@OssKx )上找到他。
*翻譯已獲得原作者授權
*本文從他本人重寫、翻譯與增訂的英文版譯出

How I found a definition of games after searching for 16 years.
為「遊戲」或「玩」找一個定義是一項非常危險的任務,但也是項非常重要的任務。這就是為什麼盡管這個話題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匹死馬,我還是決定再一次面對它,試圖在這座大廈上壘上一塊新磚。
作者:Oscar Barda
譯者:葉梓濤
原文連結:點擊跳轉
為「遊戲」或「玩」找一個定義是一項非常危險的任務。首先因為遊戲作為一個概念已存在極為漫長的時間。因此,即使我對之前的定義不滿,我也不太可能找到一些公式來超越那些比我更偉大得多的、試圖准確解釋遊戲是什麼的人。
其次,因為這可能是項徒勞的任務,字典已印好,思想已成形,所有關於遊戲定義爭論的戰場可能已塵埃落定。
但是,自從我開始發現遊戲研究的存在以來,我從未真正找到一個對我來說「可接受」的定義。因此,這是我所認為玩、遊戲、體育是什麼,以及它們從何而來的想法。歡迎在評論中禮貌地反對我的觀點(如果你認為這是個無意義的努力,我同意,所以無需再重復 :) )
這是我最初發表在Rue89上的一篇文章的翻譯、重寫和增訂版。翻譯過程也是一個改編過程,因為在法語中 le jeu(play)和 un jeu(遊戲)是同個詞。
好奇心,一種進化的工具
大腦構造的最早記錄(以我們目前所理解的)是6500萬年前。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事實證明,我們的大腦有各種支持好奇心的結構:我們都有突然做荒唐事的沖動,比如跳進水坑看看會發生什麼,建造和摧毀沙堡,對著鏡子做鬼臉……也不為什麼,真的。
但我們的好奇心同樣也是一種非常有用的進化工具:通過擁有這些沖動並對其中一些採取行動,通過培養我們探索的欲望,理解我們週遭環境,適應並生存就馬上變得容易得多。
假裝更安全
如果你一定得跳下懸崖來理解重力,盡管你可能學到了寶貴的一課,但你也不再能去教給大夥……這就是為什麼通常情況下,最好在「假裝 pretend 」的情況下進行實驗,模擬條件,試試水。堆放石子,或扔東西來瞭解重力,追逐你的寵物並與你的朋友比賽,玩打靶練習,在決定追捕巨大的猛獁象作晚餐前,這些或許是明智的准備步驟。

在較小尺度內重建我們在日常環境中所面臨條件的能力,這個想法似乎已伴隨了我們有一段時間。很容易看出好奇在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進化中發揮的巨大的作用:你認為誰的身體會更適合生存?是那隻為了取樂而不停地追逐同伴的,還是那隻一直睡到狩獵時間的?肌肉通過練習訓練。
你可能已經注意到,大多數動物並沒有真正「鍛鍊」過……它們玩。
玩是為了學還是為了其他?
所以現在可以確定:玩已經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讓我們來談談它在兒童發展中的作用。有些概念需要有基礎的領會,然後才能在很久以後被言語解釋和深入理解(比如重力、味道、顏色、社會習慣……)。
而這是如何發生的?通過玩鬧(playfulness),這正是探索與經驗語境的重構(experience recontextualised)。
但可悲的是,盡管兒童非常聰明,但如果你試圖與一個4歲的孩子談論政治,你可能會注意到他們並不真正具有成年人標準的智力……這可能是多少世紀以來,人們將遊玩、童年和浪費時間等同起來的一個原因,甚至將遊玩降低為一種浪費的、只屬於兒童的活動,不值得成年人關注。
自古以來,可以找到僅限於童年的遊玩的例子,但有明顯的例外:
包括意外的Windows XP
當我在2000年開始思考遊戲的定義並閱讀相關資料時,我第一直覺是在字典中查找這個詞。但字典的問題是,它們只告訴我們關於遊戲的普遍理解,而沒有闡明其本質。因此,它們的慣用伎倆是展示該詞出現的一系列場景:玩遊戲、扮演角色、演奏樂器……這些似乎都與電子遊戲沒有絲毫關系。於是我開始查找更嚴肅的資料。
我驚訝地發現,遊戲研究似乎相當新。
維特魯威在公元前100年寫過建築的文章,亞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35年寫關於文學的文章,盡管遊戲已伴隨我們幾百萬年了,但遊戲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並沒有真正開始(除了少數地方有些許提及)。
但當時我能找到的定義在我看來令人失望,甚至反倒增加了負擔。約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蘭人)和羅傑·凱魯瓦(Roger Caillois,1913-1978,法國人)這兩位最早解決這個問題的現代主義者列出了長長的前提條件(遊戲必須是自由的、不可預測的、無生產性、且無用的等等)。這種列舉雖然非常有用,且對我來說也是是智識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它們主要是描繪遊戲所居有的區域。在社會中的位置,似乎並沒有闡明一些更本質的真相。
在所有這些閱讀之後,我意識到我在嘗試嚴格地定義電子遊戲,相當於「一種……嗯……一種用來娛樂的……互動設備……。當你按下按鈕時,有東西會動?」
但正 Mathieu Triclot 在他詼諧的,由瑪利歐和蘇格拉底之間的對話構成的《電子遊戲哲學》(Philosophie du Jeu Vidéo)導言中所建議的,通過包含/排除(inclusion / exclusion)來定義的做法是非常沒有意義的,因為通過增加或減少概念或動詞,幾乎不可能涵蓋,如陰森的體驗、飛行模擬器、紙牌遊戲、《英雄聯盟》、《糖果粉碎》甚至由自己選擇的冒險遊戲……所有的這些方方面面。
所以我留下了很多問題。在撰寫或談論遊戲設計的16年里,當被問及遊戲的定義時,我只是簡單地敘述了定義遊戲努力的歷史,將 Juul、Bogost、Zimmerman、Lantz、Koster 和更多的人加入其中,用共同的畫筆描繪出一種寬泛的理解,但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復雜性足以讓我再也不想接近這個話題。
And then (16 years later) it struck me!
然而(16年後),我突然想通了!
「玩是做的虛構」「Play is the fiction of doing」
我無法告訴你它是如何發生的,所以如果你需要證明我並非天才,這輕而易舉:我花了16年才想出這個六個字的句子,就像偶然在我身上發生一樣。那是在夏天結束時,經過兩個月的寫作障礙,在回想這個定義問題時我突然明白了。
「虛構」是指我們參與的敘述或活動的本質,它們在尋常的現實規則懸置(suspension)的情況下存在。我們懸置我們的懷疑,進入這些經驗,並接受它們是謊言、是捏造,並觸發我們大腦中的一種特殊模式:相信卻也不信(believes without believing)。
這就是遊戲讓我們進入的模式:你追逐著球(或寶可夢),好像你的生命取決於它;你被事件打動、傷害或陶醉,仿佛它們是真的,但你知道它們不是;在你大腦的某處,有一個「現實開關」,你不想去觸碰它,但它可以在一瞬間讓你從體驗中跳出;這種懸置、漂浮的,人們可以稱之為「沉浸」的狀態,是虛構。沉浸在水中之於重力,就像虛構之於現實。
為什麼是「做的虛構 the fiction of doing」而不是「行動的虛構 the fiction of action」?因為遊戲可以包含一些很少被認作行動的事:等待、環顧四周、無所事事……以及共鳴、反思、理解,這些都是遊戲的一部分,但本身沒有行動。
因此,作為一個附帶說明(並跳回到步行模擬器的辯論中):是的,等待或四處走動是遊戲要求玩家必須做的事。它們是玩的一部分,是設計師在設計遊戲時想讓你經歷的一部分。
因此,我們要麼可以採取這樣的立場:任何遊戲中的任何等待都排除在外(這基本上將99%的遊戲逐出了這個領域),認為取決於有多少走動或等待要做(這是如此的相對主義,它使得任何定義的嘗試都是無效的,且自我否定的),要麼說:做的虛構,任何假裝的表演,任何我們參與的角色轉換都是遊玩(pl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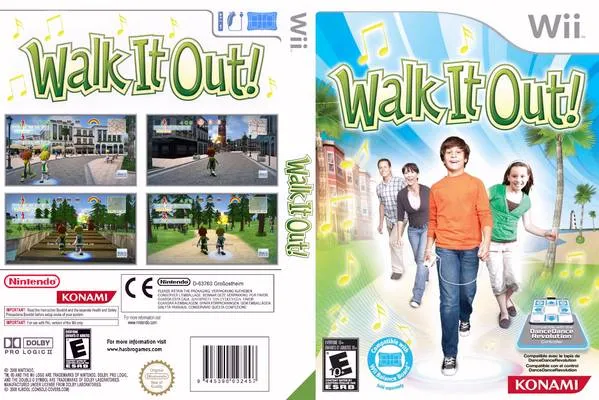
這對我來說改變了我的生活:思考玩和遊戲也囊括玩戲劇、玩音樂、玩體育和玩電子遊戲。所有這些活動,我都用了「玩 play」這個詞,但不明白為什麼。
這實際上意味著所有這些事情都是遊玩活動(play activities),在某種意義上相互聯系。玩是做的虛構:假裝某個角色,把音符寫在紙上,因為它們被你的吉他彈奏愉悅了你;編一個故事,編一個角色來測試社會世界的極限;或者扔一塊石頭,只為了看它能飛多遠。
但它們不是「視頻遊玩」(video play),它們是「視頻遊戲」,那麼遊戲是什麼?
嗯……遊戲就是玩,是形式化的。在一個虛構的狀態下,要遵循規則的設定就足可算作一個遊戲。
……等等,我們難道不想開始知道更多關於視頻遊戲(電子遊戲)嗎?它們呢?
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容易
首先,你會認為視頻會自然而然地出現。視頻,你知道的。有塊螢幕。但你知道嗎,有一些視頻遊戲是在不使用視覺的情況下玩的?例如,Papa Sangre,一個只用聲音玩的 iPhone 遊戲……它是否因它沒使用視頻而不屬於「視頻遊戲」的范疇?
你或我玩的視頻遊戲,如果被視力障礙者或盲人玩家玩,就不能成為視頻遊戲嗎?它是否變成了「只是一個遊戲」或其他東西?但他們所玩之物在本質上並沒有改變,為什麼要改變稱呼?
不,真的,「視頻作為螢幕」的線索並沒有把我帶到正軌上,特別是當你開始看到像「Johann Sebastian Joust」這樣的遊戲,這是一個現代的雞蛋競賽(你帶著一個裝在勺子里的雞蛋和其他人比賽,並在你的雞蛋不被打破的情況下試圖贏得比賽的遊戲)。JS Joust 使用電腦、Playstation 運動控製器(或之前版本的 Wiimotes),但沒有螢幕……那麼它是視頻遊戲嗎?

譯註:在 David Kanaga 《遊玩世紀宣言》筆記與計算鍊金術 中有對 Joust 的更多介紹,此外因為video game一般在中文語境下被翻譯為「電子遊戲」,所以在這里沒有他的這種澄清的負擔(在法語中同樣為 jeu vidéo 的表述)
對ALT.CTRL.GDC的考察可能會說服你,存在著數以百計的遊戲,它們由設計更多經典「視頻」遊戲的人編碼、製作和通過。

譯者附圖ALT.CTRL.GDC 是 GDC最受歡迎的社區之一,這里可以體驗不同的獨特的各種控製器來玩遊戲,可見 GDC官方頁面
實際上,這些不同形式遊戲間的共同點是使用計算機為我們做部分的工作。有時,它做一些我們可以手動完成的事(比如在電腦版《大富翁》中洗牌或擲骰子)。但在其他時候,它卻做著我們甚至做夢都想不到手工做到的事(例如在夢幻般的風景中進行大規模的宇宙飛船戰鬥)。
那麼,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計算機做了什麼我們沒做的?它計數(counts),它把我們的行為轉寫為數字,並將其轉化為螢幕上的運動,聲音,甚至是振動。它計算(computes,來自拉丁語動詞 computareto count)。
因此,視頻遊戲是一種形式化的做的虛構「formalised fiction of doing」(一個遊戲),需要計算:一種自主計算(an autonomous calculation)。這就是今天視頻遊戲的含義。當GDC是一個「視頻遊戲大會」時,這就是該術語所涵蓋的內容。
作為一名遊戲設計師,我在工作中努力追求優雅,我希望這個定義對你有用。而它對我來說當然是有用的。

我想是在《浪客行》中,一個角色說:「最偉大的畫家看著一朵花多年,思考它的美麗,然後,在一筆中,捕捉住了它的優雅」。我不是一個偉大的畫家,但我認為這個定義很簡潔地抓住了遊戲的本質。
這就是為什麼我想分享這一發現,這六個詞是我最近發現的,此後我幾乎每天都在用它。我希望你能喜歡它們,下次再提到這話題時,你可以回答:
「遊戲是藝術,就像繪畫或攝影是給人看的藝術,音樂是給人聽的藝術,而遊戲是讓人做的藝術(art of making people do)。」

松果最近翻譯了文章 Ian Bogost:為什麼「遊戲化」是胡說八道 Why Gamification Is Bullshit (2015) 後續落日間會有更多討論與回應,此外收入德勒茲研討班的 Bernard Stiegler 眼之舌:「藝術史」意味著什麼 The Tongue of the Eye: What “Art History” Means (2013) 與 Gilles Deleuze 什麼是創造行為?Qu’est-ce que l’acte de création? (1987)
日 | 落譯介計劃 是媒體實驗室落日間對一些有助於思考遊戲/電子遊戲的外文文本翻譯和推薦/索引計劃。(查看網站 xpaidia.com/sunset-project/)
感謝支持落日間的朋友們!
歡迎贊賞或贊助落日間。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