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間連結:George Bataille 我們的存在是為了遊戲嗎? 還是為了保持嚴肅?(1951)
譯按
很少有能看到巴塔耶為赫伊津哈的《遊戲的人》所寫的這樣極其精彩,深入又飽含感情的評論了。這篇很長的書評收錄在巴塔耶的全集第12卷中,在1951年的《批判》(Critique)雜誌上發表,至今還未有中譯。
毫無疑問巴塔耶非常理解赫伊津哈這本偉大著作,他看到了其中存在困惑的要害,也是赫伊津哈在《遊戲的人》結尾中留下的問題「什麼是遊戲?什麼是嚴肅?這個問題在腦海中不斷穿梭循環,弄得我們暈頭轉向」,巴塔耶試圖引入自身的哲學在遊戲-耗費,以及遊戲-勞作世界,以及與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的視角下來解答這個未竟的疑難,接續作為歷史學家的赫伊津哈無力以更靈活的思考所進入的某種辯證的區分。
巴塔耶從自己的耗費哲學的角度出發,展示自己與赫伊津哈共同的思考邏輯,並緊緊抓住了那個模糊的點「遊戲與非遊戲的分界」,他做了關於夸富宴中與「競爭性」相關的分析,並且指出了赫伊津哈的侷限在於「將禁忌之外的視作遊戲」,以及「認為遊戲就是規則」,巴塔耶認為我們更應該看到其中的某種「限度之內的失序」,以及某種不同遊戲者的「精力的限度」與「安全」的差異。
在此基礎上,巴塔耶深入到了勞動與鬥爭的對立視角中,就對死亡的恐懼,展開了主奴辯證法的視角分析,以展現了遊戲世界與勞作世界的對立。並且區分了主要的遊戲(至尊的遊戲)和次要的遊戲(屈居於勞作世界之下的遊戲)而不再至尊的遊戲只是遊戲的滑稽劇。
而之後是最精彩的部分,巴塔耶借用了弗雷澤《金枝》中的兩個例子談論了他所說的至尊與王權的關系,以此來展現出遊戲-至尊徹底的與勞動-功用的對立,並談及哲學和思想自身。
他借用赫伊津哈對《梨俱吠陀》中的思想之謎的分析,展現出思想的剩餘:謎,以及其中的遊戲與神聖性,而這也是我們常在古老寓言中遇到的:回答謎題,或死亡(如獅身人面像的謎題),思想和哲學不是過家家,也不是為理性與勞作的辯護,思想和哲學實踐是危險的,就像是尼采將哲學描述為懸崖邊的舞蹈,思想的實踐應如同一種對死亡的貼近,對理性的限制與極限的僭越,因為這本就是哲學的濫觴:
落日間
葉梓濤
George Bataille

喬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1897年9月10日 -1962年7月9日)是法國哲學家和知識分子,從事哲學、文學、社會學、人類學和藝術史的研究。他的作品包括散文、小說和詩歌,探索了情色主義、神秘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僭越(transgression)等主題。他的工作對後來的哲學和社會理論流派產生了影響。
我建議閱讀文章之間可收聽落日間播客 E36 勞作是奴役,遊戲才是至尊 ,特別感謝明德影像社群的朋友,遠在法國的 Guangni 的再次的校對幫助,讓我在翻譯原文中諸多不確定之處能夠得到回應。此外本文的尋獲過程也要感謝 Le Front 陣地 的家楨兄的幫助,
本文自法文譯出,譯者為原作分段添加了小標題,以便閱讀。
翻譯:葉梓濤
校對:Guangni
原文:Georges Bataille 100-125,發布於《批判》雜誌,由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於1946年創辦的文學、哲學和藝術月刊,由他的朋友讓·皮爾(Jean Piel)執導了50年。
封面:The Disquieting Muses – Giorgio de Chiri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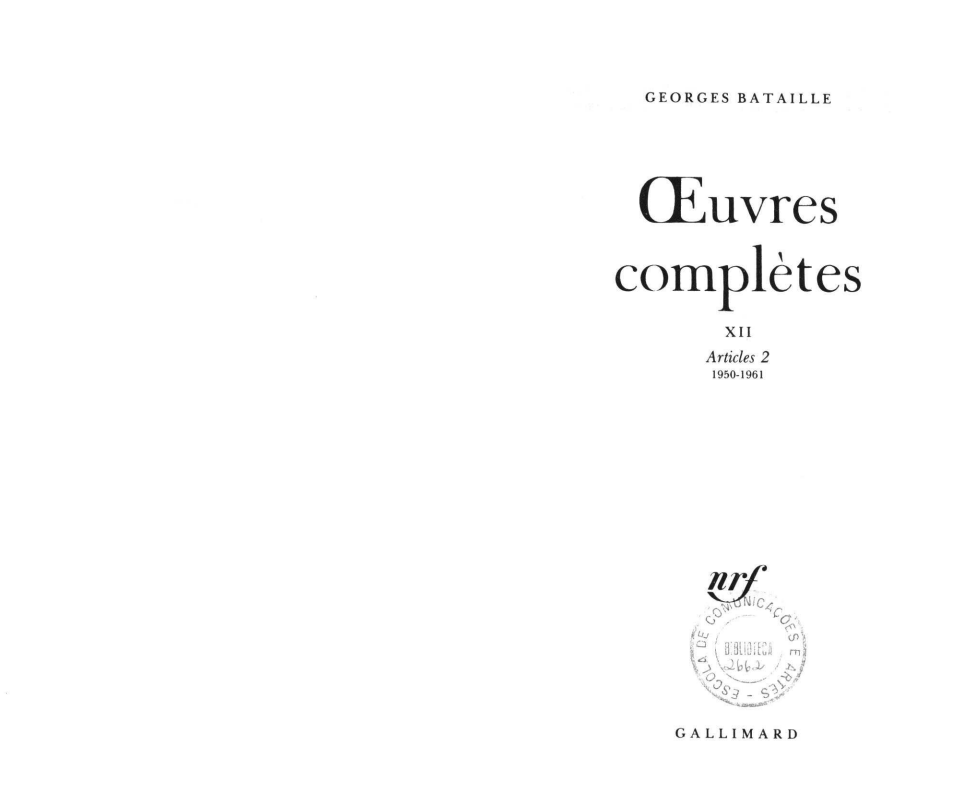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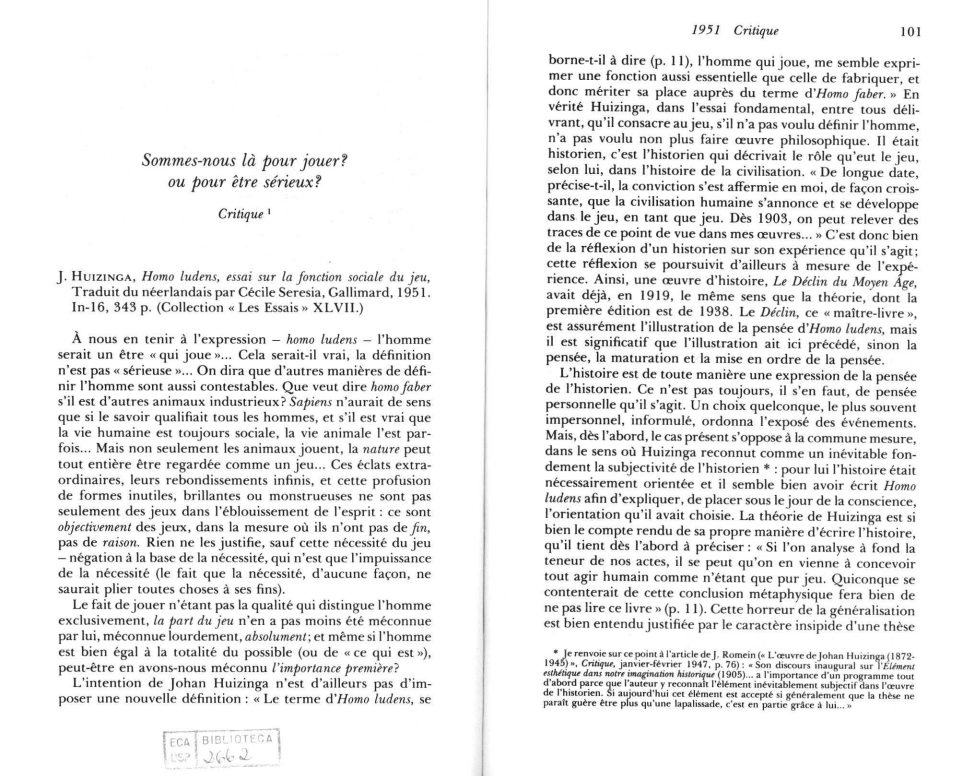
George Bataille Sommes-nous là pour jouer? ou pour être sérieux?
我們的存在是為了遊戲嗎? 還是為了保持嚴肅?
J. HUIZINGA, Homo ludens, essai sur la fonction sociale du jeu, Traduit du néerlandais par Cécile Seresia, Gallimard, 1951. In-16,343 p.(Collection《Les Essais》XLVII.)
遊戲的人
如果我們堅持這樣的說法「遊戲的人」(Homo Ludens),人是一個「玩」的存在……如果這是真的,那這個定義就不是「嚴肅的」……有人會說,其他定義人的方式也是可爭議的。如果還有其他勤勞的動物,那麼「製造的人」(Homo Faber)意味著什麼?智人(Sapiens)只有在知識能夠定義所有人的情況下才有意義。人類的生活確實總是社會性的,而動物的生活有時也是社會性的。而不僅是動物在遊戲,整個自然界都可以被看作是一個遊戲。這些非同尋常的爆發,它們的無限曲折,以及這種無用的、輝煌的或可怕形式的豐盛,不僅是精神中令人眼花繚亂的遊戲客觀上,它們是遊戲,因為它們沒有目的,沒有理由。沒有什麼可以為它們辯護,除了遊戲的必須性——對必要基礎的否定,這只是必須性(nécessité)的無能(必須性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一切事物屈從於它的目的)。
事實上,遊戲並不是專門區分人的性質,但遊戲的部分還是被忽略了,嚴重地、絕對地忽略了;即使人確實等同於可能性的總體(或「是什麼」),我們或許忽略了它的主要的重點?約翰·赫伊津哈的意圖並不是要強行規定一個新的定義「Homo ludens 這個詞,在我看來,僅限於說(p11),遊戲的人,表達了一種與製作(fabriquer)同等重要的功能,因此值得與 Homo faber 這個詞並列位置」。
事實上,赫伊津哈在他致力於遊戲那篇主要文章中,他不想給人下定義,也不想做一部哲學作品。他是一位歷史學家,正是這位歷史學家描述了遊戲,在他所說的文明歷史中的作用。「長期以來,詳細地說,我的信念越發堅定,人類文明是作為遊戲,並在遊戲中開創和發展的。早在1903年,在我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這種觀點的痕跡……」因此,關鍵在於一個歷史學家對其經驗的反思;而且,這種反思隨著經驗的發展而繼續。因此,歷史著作《中世紀的衰落》在1919年就已經具有了與1938年首次出版的理論相同的含義。《中世紀的衰落》,這本「巨著」,無疑是對遊戲的人思想的闡明,但重要的是,在這里,例證即使不是思想,也先於思想的成熟和秩序。
歷史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歷史學家思想的表達。當然,這並不總是個人思想的問題。任意的一個選擇是對事件進行有序地介紹,最常見的是非個人化的、非形式化的方式。但從一開始,眼前的這一案例就與通常的做法相對立,因為赫伊津哈承認歷史學家的主觀性是不可避免的基礎 [*]對他來說,歷史必然有方向性的,他似乎是為瞭解釋,為了把他所選擇的方向有意識地展現出來,才寫下《遊戲的人》。
(註在這一點上,我指的是 J. Romein 的文章(”L’cæuvre de Johan Huizinga(1872- 1945)”,《Critique》,1947年1-2月,第76頁)「他在 Elément estheétique dans notre imagination historique(1905)的就職演講… 它之所以具有綱領性的重要性,首先是因為作者在其中認識到了歷史學家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主觀因素;如果今天這個因素被普遍接受,以至於這個論題似乎只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一部分是他的貢獻……」)
赫伊津哈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他自己的歷史書寫方式的描述,他一開始就明確指出「如果我們深入分析我們行動的內容,我們可能會把所有的人類行動設想為純粹的遊戲。任何滿足於這種形上學結論的人都不應該讀這本書」(11)。這種對普遍化(généralisation)的恐懼當然是由一個論題的平淡無奇的特點所證明的,即,遊戲的概念因人們對它的重視而化為烏有(如果任何行為都有遊戲的意義,遊戲就會有任何行為的意義,所以它就不再有意義)。但它恰恰宣佈了一種意圖,即把問題限制在它在歷史學家的經驗中曾有過的這個確切位置。
赫伊津哈自己對遊戲的定義最正確地解決了這種實際需要。經驗所遭遇的遊戲必須保留在經驗中不可還原的意義(「這個想法不能被進一步的解釋所還原」)。赫伊津哈有理由否定那些遊戲被直接「用科學的測量工具…… 」討論的表述。
在他看來,我們必須「首先對遊戲的特殊性給予必要的關注,它深深地紮根於美學之中……」在給出的每一個解釋面前,他堅持認為,問題仍然有效那麼什麼是遊戲的「快樂」?為什麼嬰兒會高興地尖叫?為什麼遊戲者會在激情中失去自我?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固執地把冠軍推向瘋狂?從邏輯的角度來看,大自然完全可以以簡單的練習和機械反應的形式,給它的生物提供所有這些必要的消耗、多餘的能量、緊張後的放鬆的功能……。相反,它給了我們遊戲,它的熱度,它的快樂,它的詼諧(facétie)(第19頁)。
這難道不是赫伊津哈真正想要提出的遊戲理論嗎?他描繪了每當他遇到這種遊戲狂熱時,他的敏感運動就會活躍起來:他追隨著它思考,歷史學家的豐富知識引導他進入過去的蜿蜒。在他看來,這種狂熱使得這個巨大的過去充滿生機;無論如何,如果不認識到,這並不是為了滿足必須性(nécessité),而是為了滿足人類的遊戲,那我們就無法掌握這種驚人的活力(animation)[*]。因此,他認為遊戲是所有形式的文化,宗教和文字、音樂和舞蹈、司法和戰爭機構以及最後哲學的起源;只有技術,至少是在效用范圍內的生產,顯然在遊戲的范圍之外。
(註:可以肯定的是,赫伊津哈雖然對馬克思主義表現出興趣(見 J. Romein,《Critique》,1947,第80頁),但他反對對歷史進行嚴格的經濟解釋。 不過他也明確指出(Declin du Mayen Age,trans. J. Bastin, Payot, 2nd ed., 1948, p. 27, n. 1) )我的概念並不排除經濟功能,更不是對基於經濟事實的歷史解釋的抗議……事實上,這種活力是由本身無導向性的過剩(surabondance)所產生的,也由於構成過剩本身基礎的經濟條件所設定的限制,它具有了較少的導向性。)
這種大膽而矛盾的思考克服了一個基礎性的困難,這個困難來自於遊戲和嚴肅性之間公認的對立。赫伊津哈對此不容置疑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遊戲,可以上升到美與神聖的頂峰,在那它把嚴肅性遠遠拋在身後。」對他來說,神聖與無足輕重的遊戲都是真正的遊戲。他知道古人的遊戲原本是崇拜的一部分。但我們難道不應標記出從宗教形式(那里有深刻的嚴肅性)到脫離失去的痛苦的自由形式之間劃定遊戲的邊界嗎?僅僅是宗教形式才能稱作神聖,而當莊嚴讓位給遊戲時就缺失了嗎?[*]
(註:這是 Émile Benveniste 的觀點(Le jeu comme structure),Deucalion, n° 2,1947,p.161)。Caillois 在他對 Homo ludens 的研究中引用了這一觀點(dans la revue Confluences,1946; republiee dans L’Homme et le sacré,2° ed.,Gallimard. 1950.p.208-224).)
但嚴肅性遠非祭祀崇拜的固有特徵。赫伊津哈說:「孩子以完美的嚴肅態度在玩,或者可以恰如其分地說是:神聖的。但他玩,他知道他在玩。表演者入了戲(jeu)。盡管如此,他還是在玩,並能意識到這點。小提琴手經歷了最神聖的情感:他沉浸在一個超越平凡的外在世界中:但他的活動仍是一場遊戲。「遊戲的」(ludique)的特性可以合適地留存於最高等的活動中。是否可以把這個序列擴展到神聖活動,聲稱牧師在履行他的儀式時,也仍是一個在玩的人?對一個宗教承認這一點就是對所有宗教承認這一點」(第42-43頁)。「那麼,儀式、魔法、禮儀、聖事和神秘的概念可以歸入遊戲之下。然而,在我看來,把神聖的活動歸入遊戲,這並不會讓我們落入這種濫用。」
柏拉圖本人在這個方向上比他早。柏拉圖說(《法律篇》,VII,803)「我們必須認真對待嚴肅的事情,唯有神配得上所有受祝福的嚴肅,而人是神造的玩偶。因此,每個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必須按此原則,用他的生命去玩最美麗的遊戲,並達到有別於當前的另一種精神境界……那麼什麼是正確的方式呢?人們必須玩某些遊戲、獻祭、唱歌和跳舞來生活,以便取悅神靈,方能擊退敵人並在戰鬥中勝利。」赫伊津哈隨後闡明了這種觀點「神聖的行為,是慶祝的(célébrée),換句話說,它屬於節慶的框架……祭祀、供奉、儀式舞蹈和比賽、表演、神秘,所有這些都是節日的一部分。即使儀式是血腥的,對入門者的考驗是殘酷的,面具是可怖的,一切都像節日一樣上演」(第47頁)。
困難在於「建立分界點,在這個分界點上,神聖的嚴肅性褪去,變成了玩樂(樂趣)。在我們國家,一個略帶孩子氣的父親可能會因為在准備聖誕節的過程中被孩子們嚇到而變得很生氣。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一個特爾人(Kwakiutl)的父親會因為他的女兒撞見他在為一個儀式進行鑿刻而殺死她(第50頁)」。赫伊津哈因此承認,在最嚴肅的情況下,對於與儀式或神話有關的信仰,仍然存在一種懷疑,一種不真實的模糊感覺。在任何情況下,似乎都有必要肯定「在與原始神聖行動相關的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忽視遊戲的概念」(第52頁)。
我相信,在這一點上,赫伊津哈做出了正確的判斷正是遊戲的范疇有能力使任意的自由(capricieuse liberté)和魅力變得敏感,從而激起一個至尊的思想(pensée souveraine)運動,而非被必需性所奴役。赫伊津哈對至尊性及其真正表達之間的關系做了最好的澄清,他說(第54頁):「 這個神聖的遊戲領域是孩子、詩人和原始人在他們合適環境中的相遇之所。」與這個簡短而真正簡潔的公式相比,Lévy-Bruhl 或 卡西爾(Cassirer)關於原始或神秘思想的分析、皮亞傑(Piaget)關於孩童思想的分析以及弗洛伊德關於夢的分析,都有些尷尬和結巴 [*]。
(註:如果我們不考慮 Jules Monnerot 的 La Poésie moderne et le sacré(Gallimard,1944年),詩歌幾乎沒有成為與文明史相稱的思考對象。)
禮物,夸富宴與競爭
自從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著名的《禮物》(Essay on the Gift)[*] 以來,從獻祭活動到競爭遊戲的轉變已眾所周知。這篇論文後來成為許多作品的基礎。它是列維·史特勞斯(Lévy-Strauss)對亂倫問題精湛研究的起源 [**]。
(註[*] Dans M.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U.F., 1950), p. 143-279. [**] Les Structures e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e(P.U.F.,1949). ‘Voir Critique, p. 50, 簡要描述了夸富宴(potlatch)的制度,莫斯的論文也同樣是我的作品的基礎,《被詛咒的部分》(Éd. de Minuit, 1949)許多地方也與《遊戲的人》很接近。)
同樣,如果沒有《禮物》在前,就很難想像《遊戲的人》的存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印第安部落的夸富宴從一開始就像一個巨大的遊戲,對手坐在桌前,在某種形式上,全世界所有的遊戲元素和形式都在此相遇。其原則是贈禮(le don);財富和禮物在夸富宴上大量流轉,就像賭注一樣,但首先是獻祭(sacrifiés)。在一系列給予和歸還的夸富宴中(就像人們給予或歸還晚餐一樣),財富按照規則循環遊戲是在下一次宴會上歸還比自己得到的更多東西,通過奢華的炫耀,通過不可超越的慷慨來羞辱對手。這不是一個積累財富的問題,而是通過禮物增加一個人的榮耀、威望和家族的高貴。
摧毀財富甚至可能比贈送財富更轟動。讓我們想像一個遊戲,根據儀式和規則,遊戲相當於一系列越來越豐盛的筵席,直到對手必須承認失敗。
我將在赫伊津哈之後引用取自一個世界的例子,在這個世界上,所遵循的規則不必正式給出遊戲的精神,以一種引人注目的方式脫穎而出,似乎足以表現出古老的特徵。「兩個埃及吉普賽人發生了爭執。為了使之激化,他們決定,在莊嚴集會的部落面前,首先宰殺自己的羊,然後燒掉自己全部的鈔票財富。最後,其中一方看到自己將要落後,於是想賣掉自己的六頭驢,以便用獲得的現金成為贏家。當他去他家取驢時,他的妻子反對,他便刺傷了她」(Huizinga (p.107) 引用 R. Maunier (Année sociologique,1924-1925,p.811),他自己也引用了一份埃及報紙。R. Maunier 正在創作《禮物》的續篇。)
就目前看來,這是一個將拮據的活動歸還給遊戲運動的問題,而拮據的活動往往取決於因果關系的算計(只要有可能,肯定是這樣),取決於技術知識和工作。但是,回歸遊戲的運動,就是把有結果的東西等同於沒有結果,沒有任何意義的東西,簡而言之,就是至尊地行為(se conduire souverainement)。
一個人接受了他所擁有的對象的目的,他認識到在這個對象中是什麼使他服從於這個目的,他對這個對象的依戀使他,對象的主人,服從於這個目的。奴隸的主人,只要他堅持這樣做,就會讓渡他的部分至尊性他自己不是奴性的,但至少他為了利用他人的奴性而讓渡了使奴隸為他服務所必需的能量(警覺性……)。因此,阿茲特克人可以通過殺戮儀式使他的奴隸(和他自己)服從遊戲的運動,這種犧牲是不失去遊戲純粹至尊性的唯一方法,這是人類的卓越。(註阿茲特克人確實是在夸富宴的精神下犧牲他們的奴隸,夸富宴在最多樣化的層面上激勵著他們:我在《被詛咒的部分》第81- 86頁指出了這一點。)
但是,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出現在由儀式性的捐贈、夸富宴和普遍的炫耀、慷慨和卓越性的運動所指示出的轉變中。 遊戲,即對最偉大的財富的不屑一顧,是卓越的至尊,是一種對任何目的(fin)都漠不關心的方式,它只是一個通過將華貴之物的破壞或贈出來展示一個超越效用性煩惱的靈魂的機會,遊戲的次要後果是希望明顯地像其他人一樣或比其他人更出色。這不是虛榮(vanité)只有當其他人和同伴承認時,他才能完全這樣成為一個這樣或那樣的人。
但這種「承認」(reconnaissance,黑格爾的Anerkennung)最常通過競爭(compétition)實現。我們在遊戲中鍛鍊出來的追求卓越的意志,使每一種遊戲形式都具有了競爭的原則。卓越的遊戲是至尊性的破壞或贈予,是以任何非生產性地方式使用我們的資源,揮霍它們,摧毀它們,不為其他目的,只為快樂,這是與對手展示競爭優越的場合。一個無形的至尊性的形象,一勞永逸地給予,就像光的巨大遊戲主導著這些多重的努力,炫目和吞噬著無數的財富,其中的遊戲是有風險的,每個對手都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但是人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獲得優越感,只要他們的慷慨,而不是他們考量的利益。
這種限制並不奇怪沒有人在競爭中尋找關於一種工作的有效性(l’efficacité)。競爭是極其有趣的,但沒有人關心這些努力對人們的利益。如果人們公開進行鬥爭,那是為了榮耀,為了彰顯某種屬於他們的至尊性狀態,那是通過將他們的資源(或其中的一部分)奉獻給非獲利性的目的來證明的。
無論是文學還是詩歌,是歌曲還是舞蹈,是跑步還是足球,是棋藝還是牌技,是比武,是夸富宴,甚至是戰爭,參與者不擔心被視為對其利益的良好管理而狂熱:他們所尋求的超出了有關行動的目標;如果出現了,那是因為他們在玩耍,毫無緣由地揮揮霍他們的力量。他們試圖確證的優越性是玩家的優越性:它總是在於更好地耗費自己,更好地給出資源,什麼也不為。人們對遊戲世界的興趣甚至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強烈。誠然,金錢玷污了它所接觸到的一切,職業遊戲者已經失去了遊戲的純粹性,但財富對此的影響與實業家不同:財富之所以影響遊戲,是因為它會自發地流入遊戲的領域,在那里每個人的慷慨都受到激發。這是一個共同的願景,讓參與遊戲的人變得富有,而到他們時,他們也必須做出慷慨的姿態。
通常情況下,如果遊戲者如他母親般吝嗇,那他就會很別扭;毫無疑問,給他錢是很痛苦的,是把一種與他原來的慷慨相矛盾的行為引入他的體內;如果他缺少錢,這種慷慨就會乾涸!……運氣遊戲的賭注、損失和贏利本身並不違背遊戲的慷慨。因為贏家不是一個剛發了財的人:賭資並不是燙手的山芋,贏的錢對遊戲者來說只代表新的賭注,否則就是多餘開支的可能,贏家是一個幾乎沒有擁有過大量資金的人,即使在痛苦中,他也高興地像個孩子一樣對自己說:「輸了?沒輸?」他的贏利不過是他放走財富的瘋狂證明:遊戲者是一個擅長放走財富(lâcher sa fortune)的人,贏錢是這種擅長的愉快的標志,輸錢是其不愉快的標志。在任何情況下,遊戲,就其本質而言,提供了一個出眾(exceller)的機會,因此,它總是可以成為一個競爭的場合。
赫伊津哈的侷限
這方面是決定性的,它支配著整個遊戲領域的運動。然而,在我看來,這並沒有說明它的意義。雖然對慷慨的攻擊是競爭的基礎,一開始就讓步給對手是更大的慷慨,但競爭永遠不會把慷慨推到最後。最後一種觀點通常是有爭議的,因為遊戲的運動必須是可感的,對手的失敗比毫無保留地猛進的激昂競爭更重要。競爭不僅是遊戲的自然形式,它本身也可能是在遊戲精神的一部分:當仇恨和對利潤的渴望混合在一起時,它就遠離了遊戲。
因此,就其極端的殘酷性而言,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而且首先是由於對手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戰爭往往超過了遊戲的尺度。在戰爭中始終是一個充裕(exubérance)的問題,但充裕到了最後,由於投入了全部可能的賭注,它變為了貪婪,甚至在它導致敵方資源耗盡的狀態下,它淪為與遊戲最相反的反應,淪為最卑鄙自私的痛苦的陰暗反應(遊戲永遠不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遠離嚴肅性,這一點是真實的)。但這樣的戰爭只是顯出一種固有的競爭傾向。它擴大了不再富裕的競爭的醜陋特徵,但它還是表明,所有競爭中都有一個利慾薰心的因素在萌芽。
這就是為什麼把競爭和遊戲聯系得太緊密會很麻煩的原因。也許在這里,赫伊津哈對概念的處理不夠從容:有時他的眼光的敏銳性似乎被他所描繪的圖景的某種僵硬的、過度靜止的特徵所出賣了。如果作者更好地把握住變化的方面,這些動態就能更好地展現出來。秩序(ordre)也是如此,這也許和競爭一樣,都只是遊戲可以覆蓋方面之一。
赫伊津哈說(第30頁),「在遊戲領域的限制內,有一個特定的絕對的秩序」,他的結論是「遊戲創造了秩序」,「它就是秩序。」從表面上看,如果我們堅持舉其他說明問題的例子,赫伊津哈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來,有必要更仔細地考察。
對赫伊津哈來說,遊戲不僅是文化的一個因素,文化本身就是一個遊戲。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觀點,在其中再現了愉悅的、變換無常的刺激(agitation plaisante, capricieuse),沒有了這種刺激的話,擁有著技術文明的人類,就只是充滿強迫或無聊的端正的社會存在,而不是那些由給古代人類帶來豐盛生活的品味、殘酷的戲謔和焦慮的詩意所決定的生命形式。
但是,如果我們想在這個意義上判斷文化,我們必須從以下事實出發:它基本上是基於原始的恐懼(primitive terreur),其直接效果表現為禁忌的形式。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禁忌,從根本上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它們通常控制人們使其對淫穢、經血、亂倫而感到恐懼、並尊重和懼怕死亡和屍體。但是很難准確地說,這些禁忌只有在遊戲中才有意義。我們甚至有可能在這里看到赫伊津哈思想的侷限性:除了禁忌,一切都將在文化中都是遊戲。
但於此相反,我認為禁忌從一開始就見證了人類的過盛(l’exubérance);它們不是真正的遊戲,而是有用的、嚴肅的活動與那些驅使我們超越有用和嚴肅的無節制的運動之間的衝突所產生的反應。禁忌總是描述一個區分有自身規范(normes)的世俗生活有序的邊界,以及要麼規則的要麼是放縱(dérèglement)的神聖領域。一切都表明,神聖的領域和遊戲的領域在各方面都是吻合的,但有必要明確指出,如果神聖的領域是規則的領域,那麼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放縱的領域。
圍繞著每一種神聖表現的規則,都是為了在恐怖中限制和指示失序本身。因此,當國王死後,某些民眾會實行了巨大的儀式性放縱,一旦君主死亡,就會在突然間瘋狂地投入到謀殺、掠奪和強奸中。現在,遊戲總是與這種放縱的規則共同具有危險的緩和的爆炸性因素:它確實是秩序和規則,但其中的秩序和規則則證明了人們需要用規則來限制自然界不可能或難以遏制的事物的必要性。
遊戲 vs 非遊戲
從赫伊津哈非常精心的研究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嚴肅性並不是遊戲的反面,神聖的行動本身就是一種遊戲,正如柏拉圖更早時所說的。我已經表明,這並不像赫伊津哈所希望的那樣,認為「規則是遊戲的基本屬性」:遊戲在我看來,是一種有限度的失序/放縱(désordre limité)。但這樣的方法為我們對所追求的對象給了模糊而遙遠的概念。
遊戲和不是遊戲間的界限比最初看起來更難界定。從常見的反應來看,遊戲將是一種無關緊要的自由活動(une libre activité sans conséquences)…… 一隻狗欺負一隻貓,吠叫著,推搡著,似乎要用獠牙把貓咪撕碎。但他注意讓它不受傷,他只演出搏鬥中的喜劇。相反,如果它咬傷了,我們就會說它沒在玩,而且事情很嚴重(sérieuse)。
因此,這種後果會使遊戲與非遊戲的東西相對立…然後,很明顯,對狗來說,傷害甚至殺死一隻貓或一件遊戲也是一種無關緊要的行為,在它能獵殺的地方捕獵,反而比不傷人的咬人的遊戲更令人愉快。只有一種在情況下是明顯不同的:如果攻擊的動物將自己的生命置於危險之中,如果有關的戰鬥是一場生死搏鬥,在這種情況下,獵殺的狗本身也可能被殺死。不言而喻,如果狗自由地露出獠牙,這件事就不再是貓的遊戲了,那肯定會產生某種後果。
毫無疑問!但這並沒有看起來那麼具有決定性。遊戲在生死攸關的那一刻結束,這只定義了一種遊戲,或者如果你願意,或者只定義了一種玩家:會被死亡的威脅立即切斷了遊戲吸引力的人。沒有什麼比這種由恐懼導致的遊戲的無力(paralysie)更常見了。然而,我很想相信,相反,真正的玩家是將自己的生命置於遊戲之中的人,真正的遊戲是提出生與死問題的人。
我將在後面說明這些命題的基本含義。但很明顯,野生動物有機會與獵人對抗的狩獵是一種規模不同的遊戲,它在遊戲的層面上比在狩獵的層面上更有價值。同樣,在鬥牛中,越是危險的牛,或者說,鬥牛士,即殺手,在面對它時越是危險,就越是更好玩。當然,對於演員(甚至是觀眾)來說,為了達到預期目的,只有當擁有某些能量資源時遊戲才會保持原有的狀態*。
(註:因為通過一種認同(identification),觀眾自己也要消耗能量以參與到鬥牛士的感受中,他甚至可能參與到公牛的感受中……在這種情況下,他需要能量來承受後者的死亡,至少要以這樣一種方式來承受它,以免破壞愉悅與遊戲。我相信對所有熱愛鬥牛的人來說都是如此,對他們來說,沒有死亡的比賽毫無意義。為此,有必要闡明人與動物之間的深刻關系和對立。)
只要遊戲超過了玩家的力量,如果恐懼占了上風,它就不再有吸引力,它不再是一個遊戲,而是一個痛苦的行為,強迫占據了主導。這個遊戲無疑利用了參與者(演員和觀眾)的過剩能量(énergie excédante );它的前提是他們有足夠的過剩精力,不要讓他們覺得自己會被壓倒,恐怖、勉強或恐懼會太強烈。一個鬥牛士可能不會比一個因鬥牛死亡而感到恐懼的人有更多的精力,甚至是更少的精力;個體的感受差異很大,這種方式使各種行為顯得很矛盾(一個素食者可能是一個嗜血的人,而薩德侯爵發現看到斷頭台在他眼前運作是最令人不快的)。
然而,在任何情況下,遊戲都需要能量,或者說,過剩的能量需要在遊戲中耗費,這是事實。因此,遊戲的極限就是可能的耗費的極限:根據資源和愛好,這樣的危險遊戲是不是可承受的。但如果是這樣,它可以成為一條出路,最好的出路是盡可能地走遠,讓能量經受考驗,把我們引向無法容忍的極限。
在這些情況下,與遊戲相悖,死亡的風險是一種方法(démarche)的意義,它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在利益的相反方向上走得越遠越好。它從來都不遙遠,我們到達的那一點恰恰是仍然可能的遊戲,具有最大的價值,並引發最大的激情。
勞動 vs 遊戲
遊戲的吸引力的極限是恐懼(la peur):保存的欲望,保持安全的欲望,在我們身上與浪費的欲望相對立。我們每個人的天真,和隱藏的欲望是通過存續來面對死亡,通過耗費來獲得豐富。這其中不無道理,有時最勇敢的人正是因為有了面對死亡的心,才得以存續;同樣,浮華的生活方式往往有利於財富的增加。但這些浮華的方式肯定不是最好的,理性譴責了這些方法的過度。理性本身是與這種遊戲運動相對立的,這種遊戲運動激盪著人性,是它的沸騰,即使不總是快樂,也給它帶來了作為其本質的那種挑戰的情緒。
理性是一個與遊戲完全相反的世界原則:勞動(travail)的世界。事實上,它是成果的世界:勞動最正確的定義是,它修改了自然(il modifie la nature)。但它並不像鬥爭(la lutte)那樣修改自然:死亡如果是戰鬥的結果,那並不改變任何東西。它不能給自然一個新的過程,改變其現實。或者說,如果鬥爭以這種方式行事,那就是征服者迫使被征服者工作。
這些關於鬥爭(是遊戲)和勞動(是其反面)的基本方法,即使不是哲學的基礎,那也是黑格爾人類學的基礎(黑格爾的哲學本質上是一種人類學)。根據黑格爾的說法,主人(Herr)是一個承擔死亡風險的人。奴隸(Knecht)是一個不惜一切代價想要生存的人,並且接受通過在脅迫下和為他人工作來生存。
黑格爾正是從遊戲的態度(或死亡的風險)與對死亡的恐懼(或強迫下的勞動)的對立中得出了人的辯證概念。但黑格爾並沒有站在遊戲一邊。他不會像赫伊津哈那樣宣稱,文化建立在遊戲之上,或者說文化就是種遊戲。相反,對他來說,勞動是所有文化的生成器。奴隸或勞動者才是真正承擔人性的人。在歷史完成的那一刻,勞動者實現了人的可能性,並成為完成了的人,他普遍地體現了可能性的總體,並成為上帝的等同物。
必須說,與《遊戲的人》的作者相比,黑格爾的思想有一個重要的優勢它是辯證的(dialectique),在這個意義上,它從不在一個簡單的原則上,而是在多重矛盾的復雜作用中,看到現實形式的本質。繼黑格爾之後,我們可以接受赫伊津哈的方法(但赫伊津哈的方法不允許我們重走黑格爾的思想推理)。
遊戲在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從本質上講,文化一直是種遊戲,這些都是不能被否定的命題,但只有對事實的歷史性的(辯證的)表述才能讓我們把其放在適當的位置上。整個文化運動的基礎是遊戲、自由的歡騰和過度的競爭,這些非理性地把我們帶向對毀滅和死亡的挑戰。
但是勞動,即對這第一種運動的否定,顯然在一系列的傳統、行為和概念中也有一定的份額,這些傳統、行為和概念在文化的之名下,成為今天教授的對象。如果像我們傾向於做的那樣(就例如 T.S.艾略特傾向於做的那樣),認為文化是那些引誘並給予人威望(prestige)的東西,是純文學,是藝術,是服飾之美,是驕傲,是嚴謹,是思想或行為的精緻,是所有那些支撐並同時要求個人魅力的因素,那麼文化的確是遊戲的免費禮物。但這不涉及到哲學、科學和技術,以及與之相聯系的社會、法律、道德和政治行為,這是理性的范疇,而也不失為文化的一部分,它們是勞動或否定遊戲的活動的贈禮,它肯定了勞動的專屬權利,這為勞動者所應得的。
重要的是,赫伊津哈的作品所強調的,是整個文化不能被簡化為這第二種形式(勞動),事實上,這種二元性在現代文化中保持著一種令人疲憊的矛盾。赫伊津哈哀悼古老價值觀下的死亡,或者至少是衰敗。但這些眼淚是徒勞的,只是對否定的勞動世界的批判,如果這個批判首先承認這個否定遊戲的世界並非錯誤,而是因為,這個(勞動)世界的本質就是否定它(遊戲),這個批判要承認這一點,以回答人類命運帶來的問題,僅僅對過去感到遺憾是不夠的。
遊戲和勞動對立的基本特徵是非常難以提出異議的。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遊戲和嚴肅性,或者至少是悲劇和哀婉動人,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至少我們意識到,嚴肅只有在勞動中才是真正的嚴肅,神聖的或悲劇性的東西只是表面的嚴肅。勞動本身就很嚴肅,法官和法警也是如此,他們盡其所能地消除那些偶然和反復無常的因素,這些因素使悲劇即使是真實的,也有種不可否認的可怕的遊戲感。
此外,在我看來,這種與勞動的對立表明,遊戲並不像它看起來那樣,也不像赫伊津哈承認的那樣明顯地存在於動物性中。我認為,勞動對於遊戲的確定來說是必要的。
在勞動的位置之前,動物性確實呈現出或多或少接近於人的遊戲的行為,但沒有絕對明顯的特徵,使我們能夠分離出這些行為中的一個。我們最多可以說,遊戲總是接近於通常的動物行為。這些行為離休憩越遠,就越是遊戲的(ludique)。
沒有任何顛倒,沒有任何不規則的惡意,沒有任何犯罪或畸形的東西決定這些遊戲;哺育動物的狩獵和無害的戰鬥一樣,在獠牙沒有露出的情況下,也是種遊戲。只有被役的野獸或勞作的動物才會在人類的意義上工作在動物性中,只有它們才有不同於遊戲和休息的行為。但這種動物的勞作並沒有帶來節日和神聖行為的補償性反應。動物的自利活動與人的自利活動是如此的相反,以至於後者一般認為打獵或捕魚只是遊戲(至少是次要遊戲)。狩獵和捕魚是有用的行為,但它們不需要獵人或捕魚者(動物或人)的約束*。
(註:單純的捕魚是作為勞動來組織的;然而,捕魚遊戲與商業捕魚同時存在。)
它們也使人回到了與勞動對立面的動物的自由。事實上,動物永遠不會因為生存所需的活動而受苦或死亡。但是人類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勤勞,以至於他提前通過勞動來彌補了匱乏*。
(註:昆蟲的儲備與人類的勞動本質上的不同在於昆蟲的行為不回應任何概念。)
因此,從一開始,勞動就有這樣的含義:如果我們不接受在這個任務上流汗,就會擔心受苦或死亡。在早些時候,這樣的意義只能與其他不太明確的意義相聯系:毫無疑問,勞動也有審美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歷史上,對匱乏的恐懼,即對痛苦、對死亡的恐懼,通常迫使人們去勞動。但是,如果勞動在道德上被賦予了這種負面的價值(它只是最近才失去了這種價值),那是在人性被分裂的程度上,正如黑格爾所說,有些人害怕死亡,有些人想要面對它。
黑格爾說得很對,奴役(Knechtschaft)總是一個人自由作出的選擇;歸根結底,沒有人在字面上被強迫工作;限制在於是那些接受服從它的人的行為;無論是以多麼可怕的方式破壞一個人的意志,沒有人能夠持續有效的勞動:因此,勞動在一個基本方面上,是認真對待死亡的人的行為。勞動總是承認奴役狀態、服從和痛苦比死亡更可取,在生命受到威脅時,遊戲就該停止。死亡並不嚴肅,它總是讓人感到恐懼,但如果這種恐懼壓倒了我們,以至於我們為了不死而認輸,我們就會給死亡以嚴肅性,這是被接受的勞動的結果。從人類的角度來看,未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而奴役性的勞動則使人墮落和平庸,這兩者是同一個東西,是當今人類及其嚴肅言語(langage sérieux)的起源:是政治家、實業家或勞工的言語,巨大而悲傷。
兩種遊戲
由此,我們可以大致確定人在世界中的境況(situation)。他不斷被迫在兩種決定性的態度中做出選擇:他要麼玩,挑戰死亡,要麼認為死亡和世界是嚴肅的(這反映在工作的奴隸狀態上)。
但這種困境從來沒有得到足夠清晰的闡述。正是因為一個真正的遊戲要求一個同遊戲一樣巨大的暴力爆發,所以遊戲本身具有的誘惑力不再能直接在它身上體現:相反,它讓人恐懼,只在恐怖中展現歡樂。只有在與勞動相調和的純粹遊戲中,才最常看到遊戲的原則。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感謝赫伊津哈,他接過了柏拉圖的思想,在最不人性的神聖、最隱晦的可怖時刻中發現了遊戲的因素。 由於遊戲的因素本身傾向於被引入勞動中,事情就更難解開。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比支撐勞動的怯懦更讓人願意承認。因此,勞動盡可能地與脫離的態度聯系在一起,其奴性被掩蓋了:它與各種消遣聯系在一起,就像如果可以的話,在另一部分,在其主要方面,任性掩蓋了其地獄般的本質。
但我根據赫伊津哈的定義提出的這些定義,顯然可以讓我們走出困惑。遊戲問題的困難性在於,同樣的名字下實際上指向的是非常不同的現實情況。一方面有次要的遊戲,它在接受勞作之人的屈從中倖存下來,而絕非要求完全的反抗,這是沒有死亡憂慮的挑戰。這種遊戲只是被嚴肅主導的生活中的一種放鬆,而嚴肅總是比遊戲更重要。如果我們給一個富有的實業家一首詩,只是一個真實占據了主要地位並且全然至尊的遊戲,他會發笑,或給予禮貌的冷漠回應,這個龐大臃腫的行動中,真實占據次要地位,並由使世界屈從於勞動的痛苦組成。
對一個有秩序的頭腦來說,舉止行動中所表現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強迫、認命、痛苦、汗水或對恐懼的屈服都不算什麼。這就是最終超過了這個世界上國王的威嚴的東西。使得遊戲的天真運動無力的痛苦的勞動原則,現在成了至尊的原則。
在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情況能更好地回答尤文納的公式:「Et propter vitam, vivendi perdere causas……」(譯註:還有前半句為 summum crede nefas animam præferre pudori,整體含義為:寧可活下去而不顧榮譽,為了生命而失去生活的一切理由,這是最大的罪惡)。
為了維持生命的意義而失去,這就是勞動的至尊性(souveraineté)所宣佈的,它使一切都服從於對死亡的恐懼。這些小遊戲,這些高爾夫球場和組團旅遊,這些軟弱無力的文學和缺乏生氣的哲學,都是一種巨大的放棄讓位(abdication)的方式,是這種寧願勞作也不願死亡的可悲人性的反映。這些在世界所有苦活中浸泡過的頭顱,罕見地爆發出自豪感,但普遍的共識使得他們傾向於:一個最高的價值,一切無用的東西都應受到譴責;而遊戲,由於其本質是無用的,所以必須降低到放鬆的次要功能,而它自己則傾向於有用的活動,至少在這個意義下是有用的。
這些原則否定了戰爭作為一種主要遊戲,當然,從總體上講,也否定了其作為一種遊戲。坦率地說,戰爭完全是從效用的角度來看待的,是一種防禦性的行動,沒有這種行動,一個國家的生命就無法存續下來。由於這種價值判斷不僅與傳統相悖,而且與假定的死亡風險的遊戲性質相悖,戰爭迅速演變為勞動的形式;戰爭現在是一種與其他勞作相類似的勞動,受制於勞動的原則,也就是強迫。
這就是畸形的矛盾,它把一個不再理解的人類置於不可生存的標志之下。這些被迫從事戰爭勞作的大眾不能說他們寧願勞動也不願死亡:從今以後,勞作和死亡同時成為他們的悲哀。但是,承擔死亡的風險在自由渴望的遊戲中已不存在。
簡而言之,奴隸們殺死了主人,但他們不得不集體追隨他們中那些拒絕他們的身份,且寧死不屈的人:領導者們只能把主人的身份強加給他們,而大眾已經放棄了。由於領導者往往不願意自己充當主人,這種困難就更嚴重了。(然而,在拿破侖的帝國里已經發生了這種情況。)
他們不能從死亡的危險中得到那作為遊戲特點的巨大生命運動:他們不能在他們周圍傳播那些榮耀的原則,這些原則吸引著戰士們參與進這運動。他們不得不宣揚相反的真理,這些真理宣稱了勞作的首要地位。毫無疑問,在戰爭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可以感覺到遊戲的因素,沒有人敢於或能把其作為次要真理。 但是,什麼都不說很容易,或者至少不堅持。首先,有必要肯定新世界的原則:有用是唯一的至尊,只有在提供服務的情況下,遊戲才可被容忍。
因此,今天說相反的話是矛盾性的:有兩種遊戲,主要的(majeur)和次要的(mineur);在一個有用性是至尊而非遊戲的世界中,只有次要的遊戲,由於這個原因,我們最熟悉的莫過於不能提供服務的主要遊戲,而其中展現出了深刻的真理:除了遊戲之外,沒有至尊,不再至尊的遊戲只是遊戲的滑稽劇。
至尊與王權
這一真理首先將可觀的清晰度引入了晦澀的遊戲領域,但同時它也照亮了一個不容易穿透的領域,那就是至尊性(souveraineté)。
遊戲和至尊性密不可分。事實就是如此,一方面,王權的原則在與遊戲的首要性相聯系之前仍然是難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及國王的行為(從黑格爾的角度來看,是主人的主人),我們就無法充分描述遊戲。
王室成員不僅在其消遣(agrément)的意義上致力於遊戲:他不僅是遊戲的主體,也是遊戲的對象。遊戲對他有控制權;他事先受制於神聖的行為,而無權挑戰它們的權威。
弗雷澤(Frazer)提到過印度南部奎拉卡爾省的一位國王:「……這個省由一位國王管理,從一個禧年到另一個禧年,壽命不超過12年。他的生活方式如下:在十二年期滿時,無數的人群在這個節日的當天聚集在一起,很多錢都花在了婆羅門的餐食上。國王做了一個木頭平台,上面覆蓋著絲綢掛件;然後他在一個水箱里以極大的儀式和音樂聲洗澡;之後,他走到神像前,向它祈禱,爬到地板上,當著全場觀眾的面,拿起鋒利的刀子,開始割他自己的鼻子、耳朵、嘴唇、四肢和盡可能多的肉;他把所有這些身體的碎片都扔掉,直到失血過多,開始昏厥;然後他割斷自己的喉嚨*。」
(註:《金枝》,第256-257頁,我必須提到由弗雷澤女士翻譯的節選版。)
我懷疑我是否能舉出一個更能說明遊戲的主權和違背了支配這個勞作世界的行動原則更遠的例子。但我們被這種如此完美的瘋狂所淹沒,要把它理解為我所說的遊戲行為的標準,似乎也很難做到。
另一個儀式則不是這樣,弗雷澤也給了我們這個故事
「卡利卡特國王用他的王冠和生命作賭注的節日被稱為 Maha Makkam,即大祭祀。它每12年重復一次……儀式在位於 Ponnani 河北岸的 Tirunavayi 寺廟隆重舉行,就在現在的鐵路線附近。從火車上,人們可以看到一點寺廟,它幾乎被河邊的樹木所掩蓋。從寺廟的西側門廊開始,一條完全筆直的道路向上延伸,稍稍高出周圍的稻田,兩旁是壯麗的樹蔭,在七八百米之後,它遇到了一個陡峭的山脊,在上面仍然可以看到三或四個平台的輪廓。
當決定性的一天到來時,國王在這些平台中最高的地方占據他的位置,那里提供了一個令人羨慕的視野。穿過河水流淌的稻田平原,寬闊、平和、蜿蜒的河水,人們的視線來到了有著片狀山頂和森林覆蓋的山坡高山上,而在遠處可以看到西加提斯的巨大山脈,還有更遠處的尼爾赫里斯或藍山,它們幾乎要融進蔚藍的天空。
然而,在這致命的時刻,國王的目光並沒有轉向遙遠的地平線。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個更近的視線。在下方,整個平地上涌動著軍隊;軍旗在陽光下歡快地揮舞著;無數營地的白色帳篷在綠色和金色的稻田中格外顯眼。四萬或更多的戰士在那里,聚集起來保衛他們的國王。平原上布滿了士兵,但那從神廟到皇家平台的那條橫穿平原的道路則空無一人。沒有一個人在其上移動。路的兩邊都布滿了柵欄,兩條長長的長矛樹籬穿過,被強壯的手臂所指,在空曠的道路上聳立,鐵器在閃光中交織,形成堅固的鋼鐵拱頂。一切都准備好了。國王揮舞著他的劍。
在同一時刻,一條用凸圓形寶石裝飾的純金大鏈被放在了國王身邊的大象身上。這就是信號。寺廟門廊周圍立即出現了一陣騷動。一群裝飾著鮮花、抹著灰燼的角鬥士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他們現在正在接受朋友們的祝福和告別。再過一會兒,他們就來了,從長矛的過道上走下來;他們在長矛所指的方向上左砍右刺;他們在鐵器中滑倒、轉身、扭動,仿佛他們身體的骨頭已不存在。一切都是枉然(stérile)。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倒下;有些人靠近國王,有些人離得更遠,他們滿足於死亡,不是為了王冠的陰影,而是為了向世界展示他們無畏的勇氣和能力,純粹的驕傲。
在節慶的最後十天里,同樣的壯麗勇氣的展示,同樣的徒勞無果的人命犧牲,被不間斷地重復*。」
這次我可以問自己,面對死亡如何能更清楚地承擔起遊戲的意義,最高的遊戲與至尊的獻祭不再有何不同,它明確地展現了它的意義。
(註弗雷澤的結論是:「然而,如果它證明了有一些人寧願選擇榮譽而不是生命,誰能說這些犧牲都是絕對徒勞的?這就是印度奈米的牧師命運的平行情形。」)
革命,戰爭
沒有什麼能比這表示與功用世界更截然相反的行為了。
然而今天,如此深刻的運動的影響不再被感受到。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革命」運動本身,即創立並仍在創立用有用的東西取代榮耀之物的首要地位,其起源於與主人相似的拒絕。然而,革命者並不拒絕勞作,但他不再接受為剝削他的個人的利益而勞作:他想消除勞動中的強迫部分。因此,他要求擁有自己的至尊性生命的權利,准確地說,一種不再從屬於另一個人的遊戲的生命,而這並不等於是他自己的遊戲。
另一方面,不可能否認革命時期的君主早已失去了他的部分的真正至尊性。事實上,這位君主不得不耗費其臣民的部分資源來進行遊戲。在這個意義上,他不僅不再是臣民的玩物,也不再是自己的玩物:他把行使王權作為一項勞動。為了玩得更好,他不得不停止玩耍!他不得不說話,對勞作世界作出許多讓步,給這個至尊性的遊戲以理由,而其本質恰恰是毫無理由。 他不得不撒謊,他既沒有力量也沒有心思向工人承認,他的快樂是他辛勤工作的唯一目的。反過來,他對至尊性所做的,就像工人害怕死亡而首先對自己的生命所做的那樣:為了顧全它,他失去了使其變得有意義的東西。
因此,革命者有理由不再玩一個在其完整性中不再具有遊戲意義的遊戲。在另一種意義上,有必要嘗試(和窮盡)屬於至尊性的勞動者的矛盾形式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如何想像,理性和功利的計算有一天不再有在其手段范圍內不受約束的行動能力?現代世界及其非凡的力量誕生於一種甚至不可能被推遲的經驗之中。
但摧毀遊戲和至尊性世界的行動並不是毫發無損的。把財富從遊戲中拿出來,完全用於勞動(用於工作和生產資料的積累),資產階級不得不在道德上毀掉那曾是遊戲、高貴和至尊的一切形象。但最終,這只會導致可用於遊戲的資源量不成比例地增加……因此,我提到的現代戰爭的無力(impuissance):不可能無休止地積累的過度積累的財富,只能被那些被那些害怕死亡、而無法遊戲的奴隸們耗費。事實上,還有什麼比這些至尊性的屠殺或者無人不受約束更可憐的呢?在這些巨大的死亡行為中,每個人都害怕死亡。
哲學與謎
在我看來,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遍戰爭最後似乎以不相稱的方式表達了人類的主要矛盾:人類只是來玩的,而卻把自己交給了嚴肅的勞作。我想最好不要過於堅持這一點:在這個時候這麼說可能很可惡,因為它使我們倖免於難,但人的苦難(misère)是表面的。
這首先是一個思想問題:苦難和死亡對動物都沒有任何影響,動物不會被苦難或死亡的威脅所強迫。這使人更加明白,思慮(penser)痛苦或死亡和被迫陷入它們之間沒有區別。想像就已經是勞作了,它是通過勞作來認識死亡和痛苦,並屈服於它們,而正是勞作奠定了思慮的法則。
相反,思想(pensée)對拒絕死亡和痛苦脅迫的生命運動感到不安;思想在本質上是對遊戲的否定和主動性的反對。這一點必須得到強調。思想不僅在根本上是理性,不僅打擊與理性相悖的東西(即至尊的、起伏不定的、無用的東西),不僅在建立在有用性和約束性基礎上的操作范圍內困住了揮霍的運動,而且還傾向於把自身限制在勞動的輔助作用上。
這個問題值得再次考慮,這次是根據赫伊津哈的分析。
如果思想為勞作服務是真的,那麼沒有思想就沒有勞作,沒有勞作就沒有思想,那麼這也會最終產出謎語般(énigmes)的剩餘,且不能認為謎語與思想完全相異。然而,對謎語的思考使思想離其起點如此之遠,以至於當我們看到它以遊戲的形式表現出來也無需驚訝。
通過閱讀赫伊津哈的文章,我們瞭解到,在古代文明中,這種謎語遊戲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赫伊津哈談到了「祭祀的謎語競賽」。他寫道(同上):「在偉大的莊嚴祭祀中,這些競賽與祭祀本身一樣構成了儀式的基本要素。」這種功能在吠陀傳統中最為明顯:「《梨俱吠陀》中的幾首歌曲包含了這種競賽的直接詩意生產。在《梨俱吠陀》贊美詩 I,64 中,有些問題與宇宙現象有關,有些問題與祭祀的儀式特徵有關:我問你地球的盡頭,我問你地球的肚臍在哪里。我問你關於種馬的精子;我問你關於理性的巔峰。這些歌曲中普遍存在的是具有儀式性質的謎語,其解決方法取決於對儀式及其象徵的瞭解。但在這種謎語中,關於存在的原因的最深刻的智慧正在形成」(第178-179頁)。
赫伊津哈在這方面引用了「宏偉的贊美詩」(l’hymne grandiose, Rigveda,X,129),根據 Deussen 的說法,這可以說是 「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最令人欽佩的哲學思想片段」:「那時沒有存在,沒有非存在。它上面既沒有大氣層也沒有蒼穹。什麼在移動? 在哪里? 在誰的照顧下?深淵的深處是否充滿了水?-沒有死亡,也沒有不死亡;沒有白天和黑夜的區別;只有「那」(le Cela)在獨自呼吸,不產生風;也沒有其他東西存在」(第179頁)。
赫伊津哈補充說:「面對這些在存在的奧秘面前高揚原創思想和情感的作品,我們不容易區分神聖的詩歌、接近瘋狂的智慧、最深的神秘主義和神秘的語言文字。這些古老的牧師-歌者的話語不斷浮現在不可知的門前,但這些門對我們來說仍然是關閉的,正如他們一樣。可以說,在這些祭祀競賽中,哲學誕生了,不是從一個虛妄的遊戲中,而是在一個神聖的遊戲中」(第180頁)。
此外,這個新生的哲學遊戲的主要特徵是從:死亡的風險(le risque de mort)中誕生的,這也是我所認為其掌握了遊戲本質的元素。赫伊津哈自己說:「謎語揭示了它的神聖性,即「危險性」,因為在神話或儀式文本中,它幾乎總是以「落在頭上」的謎的形式出現:換句話說,回答者的生命與對其的解決有關,這構成了遊戲的一部分」(第182頁)。許多故事都證明了謎語的地位和猜測者面臨的死亡之間的這種聯系,不管是不是神話。希臘傳統本身就深諳賜予給失敗者死亡承諾的事實。
這種以不可知和死亡來衡量人類自身的雙重特性,標識了的哲學誕生,今天仍可作為哲學思想與科學思想相對立的標志出現,就像遊戲與勞動相對立一樣。但在歷史上,哲學並非被限制在這種遊戲的運動中。它把自己放在了勞動的一邊,並在無法解的謎語的層面上,把自己交給了在與積極經驗相聯系的知識層面上表現出色的方法。
因此,一個越來越嚴肅看待自己的「哲學世界」不僅沒有保留遊戲的部分,而且還與任何與理性格格不入的價值作鬥爭,將思想以及隨之而來的行動,投入到當前人類的死胡同之中。在這一點上,可以開始對黑格爾的批判:黑格爾沒有忽視思想的困難,他想把一切都歸結為勞作,在此意義上,他尋求勞作和遊戲的一致。在我看來,黑格爾有一點是對的:只有當勞作的可能性發展到極致時,必須是至尊的遊戲才能在思想中找到一席之地。
讓我們在這方面說,就其本身而言,在行動(勞作)層面,戰爭在我們看來是以自己的方式達到了這種極限。也許這就是赫伊津哈這本小書的及時性:建立在勞作和約束基礎上的思想已經破產了;現在是時候了,在給出了勞作、有用性、以及這些我們太過熟悉的畸形部分之後,自由思想終於記起,在內心深處,它是一個遊戲(一個悲劇性的遊戲),整個人類和它一樣是一個遊戲,而只是通過忘記了這件事,而獲取了無數垂死之人、無數戰士的強迫勞動……
那些生產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機器的實驗室里的研究成果成功指明了這種讓勞動無限制地成為至尊性現實的災難特徵。
結語
如果人們願意跟隨他的小書所開辟的視角進行廣泛的發展,那麼我不得不對赫伊津哈的一些解釋提出這些意義不大的保留意見。最後,我要補充的是,對我來說,我很難不對一個寫下這樣句子的人送上我的贊美,他寫道:「要理解詩歌,必須能夠領會孩童的靈魂,就像穿上一件神奇的衣服一般,並承認,孩童的智慧比人類的智慧更加優越」(第198頁)。

E36 勞作是奴役,遊戲才是至尊
日 | 落譯介計劃 是媒體實驗室落日間對一些有助於思考遊戲/電子遊戲的外文文本翻譯和推薦/索引計劃。(查看網站)
感謝支持落日間的朋友
歡迎贊賞或在愛發電贊助落日間
來源:機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