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兄弟姐妹,外公外婆……血緣帶來的親屬關系為個體的人生編織了網,孤獨、寂寞、傷感被逐一分散、吸收、重製而後返還,於是笑容溫暖了你我。那時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因新生命即將誕生與誕生後的喜悅的延續來自於心中的熾熱原欲——愛——它從《ZED》中跳了出來,用時間軸將我溫柔捲起。
這是款步行模擬遊戲,一個較難產出的遊戲類型,或者說一個受眾較窄的遊戲類型。很顯然,在如今追求速度與激情的快感節奏中,即便是那些標注著冒險與探索的遊戲類型,都在角色扮演與酷炫的動作中適應了市場需求——給玩家帶來優質的視覺沖擊和精神刺激。不可否認,快感這種增強現實的東西在青少年的身心發育中存在著重要作用,它確實能夠將一部分性沖動轉換,並返還給自體享受,帶來快樂,但精神活動總是一個「多民族統一」的整體,就像你不只需要會講母語,也要耳濡目染,或是精通一些地方語一樣。
所以說,在追求這種快節奏的短暫快感後,我們是否也該為精神世界添上一些慢節奏的快感,來體驗、思考、尋找一下心中的那片遺忘、被遺忘的平靜世界?

《ZED》雖說有17.4GB的大小,但作為一款步行模擬遊戲來講,它幾乎將所有的一切都獻給了它——為呈現最大化的視覺享受。由於該遊戲類型較冷的原因,在選擇對比時往往能很快的找到同類型的作品,所以筆者很快得想到了前不久推出的另一款遊戲——《屍靈》。雖然它在沒玩之前給人一種冒險、懸疑類型的感覺,但在體驗後我們知道,這種感覺完全體現在劇情、題材與驚艷的音樂結合後所營造的氛圍當中。拋開這些後,它就是一款實實在在的步行模擬遊戲。當然,它的表現確實很出色。
視覺上的《ZED》與《屍靈》
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覺享受,一個在外部,一個在內部。對於步行模擬遊戲而言,既然是為了帶來最大化的視覺享受,那麼「第一人稱」必然是最為合適的遊戲視角,而又由於《ZED》「進入夢境」題材的特殊性與較少的遊戲交互的原因,「你只需看著螢幕世界就好,不需要看到自己」。靜謐的樹林小屋、深夜的喧嚷車站、靚麗的夢中樂園……看一看,聽一聽,構成了它旅行般的遊戲體驗。我們說在整個遊戲中,觀賞和聆聽(旁白)成為了它主要的感官享受。

這是該類型遊戲最為常見的遊戲視角,相比於第三人稱具有更強的代入感與沉浸感。不過對於此類型遊戲而言,在視覺享受之外,時不時的旁白與語言交流往往起著承上啟下、說明劇情發展情況的作用。可惜的是,該作雖然具有一流的視覺體驗,但卻由於不支持中文的緣故,使得國內玩家在遊戲中感到十分痛苦:再也沒有比在遊戲中看不到中文翻譯更為難受的了。在這點上,《ZED》雖然將玩家帶入到了遊戲世界內部,盡情的在視覺體驗上表現了一番,並達到了顯著的效果,但對於英語聽力不太好的國內玩家而言「在看到近乎真實的遊戲世界時,耳邊響起的英語除了帶來煩躁外,還是煩躁。」反觀《屍靈》則大不相同。

《屍靈》需要玩家在遊戲中進行不同程度的操作,因此才有著人物建模的存在,具有更強的交互性,所以在對比《ZED》那種舍棄人物建模,直接使用攝像頭來觀看、探索世界的方式時,這種「更強的交互性」更像是一種在遊戲世界外部的體驗。況且,該作支持簡中語言。當然,內外之分並不僅僅在此。在交互性帶來的區分外,遊戲劇情的展開場所也是一個原因。在《ZED》中,基於「為老藝術家尋找記憶碎片」的這一目的,所有的探索和解謎都在一個夢境中展開,偏向於「收集」要素,而這個夢境其實一直存在於一戶房間內;《屍靈》則是在一座海岸的村莊中展開故事,需要「探索」和「冒險」的要素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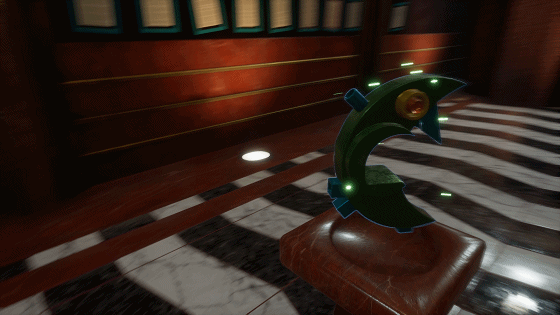
故事上的《屍靈》與《ZED》
如果說《屍靈》是在謊言中完成一場面向心靈救贖的真實旅程的話,《ZED》就是在尋找個人成長前後中血濃於水的愛。一個跌宕起伏,一個風平浪靜。
倘若你瞭解弗洛伊德與克萊因,或是讀過他們的著作的話你就會明白,《屍靈》就是在講述一個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痊癒過程。這種病症的形成很復雜,用精神分析心理學談的話勢必會涉及到「先天性體制根源」與個體發展過程中:性與精神堤壩的形成與關系。我們大可不必去瞭解它是如何形成的,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歇斯底里症最大的特點就在於:一個謊言偽裝下的真實。這點在遊戲劇情的結束時被完全的展現:所有的一切都是源於伊麗莎貝(男主妹妹)到來的這個謊言而引發的一段真實救贖。不過這個真實並不只表示救贖,它也在訴說著海岸村莊人民為何消失的真實原因,並在其中將謊言與真實放到了起伏跌宕的故事中不斷的穿插,最終呈現出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挪威小世界。

可以說《屍靈》在故事上嚴格的遵循了歇斯底里症發病特點的這一事實,然後在劇情上構造出升騰跌宕的遊戲體驗,當最後真相被解開後,緊繃的腦神經獲得滿足,刺激得到釋放,快感噴涌而出。
其實心理學在遊戲中的運用太過廣泛,尤其是在恐怖題材的遊戲中。它正是利用人類的思維盲區,將未知世界的壓抑與心理中的壓抑結合,最後完成沉積後的精神解放。當然,這在3A作品里也有涉及,例如在即將發售的《死亡擱淺》里,黑白世界與分裂的世界或許就用到了「死亡驅力」與「主體一致性」的問題,當然後者已經上升到了哲學范疇。
總的來說《屍靈》的故事之所以能夠讓玩家喜歡,是因為它在通過冒險故事來還原一個心理病症恢復的過程,而眾所周知,心理問題是人體精神上的本質問題,處理的好並讓劇情充滿曲折的話自然可以贏得玩家內心的情感共鳴。

那麼,《ZED》呢?
它並沒有前者那麼的復雜與跌宕,也應該沒有涉及到心理學的學說與派系,它只是在用事實去闡述著一個用任何知識理論都無法解釋的情感——愛。
起初筆者認為:既然《ZED》發生在夢境中,那麼它是否會涉及到《夢的解析》里關於夢境方面的「潛抑作用」與「轉移作用」?其實並沒有,它並不像《屍靈》一樣將自己放在了一個主導者的立場角度,有著明確的任務與目的,而是充當起了一個引導者的角色——先是將玩家帶進夢境中並將夢境蓄滿愛,然後一步步地引導著他們去自發性的探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這種「探索」與開放世界中的探索很像,但它沒有宏大、華麗的世界與有趣的故事、玩法,它很平淡,平淡到你一開始就想舍棄。

從個體生命誕生並獲得玩具開始,那個玩具中就已充滿了愛,此後的生活只是在一種供給需求的關系中不斷的在天秤維持著它。這種經濟學的角度真的太過冷酷,不過我們的生活經歷好像確實是這麼對待它的,快樂的砝碼重一些,悲傷就輕一些;悲傷的砝碼重一些,快樂就少一些。而當它進入《ZED》里後,車禍、葬禮、獲獎、禮物……事例在劇情中被一一列出,伴隨著歡呼雀躍與悲痛莫名的旁白,在平靜中讓人感到生命的寶貴與脆弱。於是愛出現了,將我們從這個天秤中釋放了出來。
在《ZED》的整個遊戲中,除去那首在接近終章時剎那間喚起記憶中母愛的《hush,little baby》之外,該作並沒有添加任何音樂。因為愛本來就沒有音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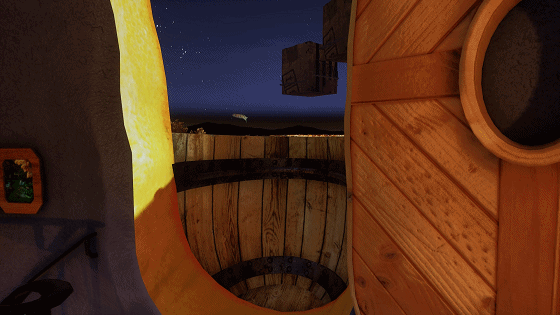
一般來說,一款單機遊戲若是缺少了音樂的話根本無法現象,即便是一款步行模擬遊戲。然而《ZED》由於題材的特殊性,去掉音樂反而讓人生的哀與樂更加容易走入玩家內心,留下深刻的印象,勾起自身深處的記憶,最後使得平靜世界更加平靜。頗有種「此時無聲勝有聲」的感覺。這也是為什麼會說《ZED》很平淡。它所尋找的是那片在遊戲世界中快要被遺忘的平靜世界,而這往往是需要個人去靜靜體會的。
記得伊萬在成為絕地武士前,在電影《奏出新希望》中送約會的女士回家時有著這麼一段對話。
女士:「想要進來喝一杯咖啡嗎?」
伊萬:「這是個問題,我不喝咖啡。」
女士:「這不是問題,我也不喝咖啡。」
它就像是在這樣的告訴我們一樣。
「想要來玩一款步行模擬遊戲嗎?」
「這是個問題,我不玩這個。」
「這不是問題,我也不玩這個。」
步行模擬遊戲的吸引力是從內向外的,在外在上它並不具備主流遊戲類型的強大吸引力,你只有主動的去玩,去靜靜地體驗,才會知道,才會明白它所包含的樂趣和意義。

總結
在評測此類型遊戲時,故事性往往是最重要的一點,所以當去評價它時很難不做到劇透,這是該類遊戲十分煩人的一點。該遊戲劇本由曾經創作出《生化奇兵3無限》劇本的作家喬·菲爾德創作而出,可見在哥倫比亞城「文藝」之後他又來《ZED》中「愛」了一把。
雖然該作整體表現不錯,但兩個多小時的流程確實很短,且太過注重於展現「兒童」、「少年」、「青年」等成長發育中的各個階段,導致整個劇情的連貫性不強,有些僵硬。不過它仍不失為步行模擬遊戲中的一款佳作。
我們縱深而入,在grandpa的夢境中重拾他的記憶,當把四個玩偶放入一個夢想後,一本送給未出生孫女——夏洛特的童話書終於完成。
「The world is anything she can imagine.」
「Where is Charlotte?」
…
「I love you.」
This is Love.
來源:3DMG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