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張藝謀素來是一個爭議纏身的導演,就連chatGBT都能察覺出些異樣,從《英雄》之後,張藝謀就從一個「風格明確的中國優秀導演」變成了一個「風格捉摸不定的爭議導演」(chatGBT語)。「捉摸不定」也可以換種說辭,叫「風格多變」,這便是張藝謀近些年的人設(之一)。所謂「活到老,學到老」,七十三歲的老謀子還在不斷挑戰自己、走出舒適圈、嘗試新事物(《懸崖之上》是張藝謀首部諜戰片、《堅如磐石》是首部犯罪懸疑片、《狙擊手》是首部春節檔電影雲雲),理應得到嘉獎,可對於老頭子的批評仍然不絕於耳——主要是失望,對於影迷來說,張藝謀理應在國際上大放異彩,拍出更多質量上乘的文藝片,繼續他的審視與反思,而不是像現在……唉,一聲輕嘆,張藝謀的轉變似乎預示著一個時代話語的轉向。一個官人模樣的金字招牌,一個國師。
然而——即便沒有張藝謀,哀嘆也不會消散,即便這個位置換成其他人,失望也不會缺席。無論你是否喜歡他都不能否認,「張藝謀」這三個字已經與中國電影密不可分了,而談及電影,文藝片又不過只是一個門類。與其說人們珍視電影,不如說珍視說話的權利。而在這片土地上談論任何藝術的高昂,都無法繞開沉積已久的政治,若藝術僅是反擊的矛頭,那也不必說自己是藝術的信徒,而因此對老爺子失望,也只是一廂情願的相信,決不投降的才是藝術家的風骨。若此,俄國沙文主義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該被罵死,然而並沒有。倘若司馬相如活在今天,也會被罵成溜須拍馬之輩,而不是漢代大賦的集大成者。將電影等同於藝術,本身就是不公允的。電影實在特殊,拍過一次的人就知道,如果沒什麼錢,最好不要碰;如果無法服眾,也最好不要嘗試,除非是百年一遇的奇才,什麼活都能幹利索,可如果電影是為天才而生的,那麼也不存在什麼「電影業」了。在拓寬看待電影的視野後,或許能對張藝謀有個更為體面的認識。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張藝謀很難被稱得上真正意義的電影大師,他的作品從來不是吸引我的關鍵,可他拍電影的歷程,卻著實有趣,透過張藝謀的影像,可以直觀呈現改革開放後中國電影的變化,這種歷史價值,是獨一份的。而正是因為身處時代漩渦中,使得電影之於張藝謀曖昧不清,特別是他作為大陸電影的領軍人物,常常被擺在明面上,接受各方審視。在九零年代前,他是先鋒電影的代言人,之後又回歸影戲傳統,逐步確立其地位。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作為產業的電影在不斷探索自己的方向,而這同時也是張藝謀的自我改革。他既是導演,也是明星,既是大陸電影的代表,也是電影(行業)探索的先驅。擁有極高聲望的張藝謀,已然不能像個愣頭青一樣不管不顧。他被捆綁在時代的列車上動彈不得,必須由他邁步,也只能靠他邁步。相較於活在自己世界的陳凱歌來說,張藝謀確實是個善於求變的人,也更懂得審時度勢,是個聰明的中國文人。從渾身野性到成為「國師」,對於張藝謀而言,這種轉型無疑是成功的。難道屈原與李白不想成為國師嗎?想,但沒成,所以藝術成就很高。理想的傳統文人身上固有三種身份:詩人(才華)-知識分子(學識)-官人(權力),三位一體,不可缺失。而其中最重要的,則是與政治的親密聯系,若不愛惜權力,李太白為何執意要在長安城中大展拳腳?懷才不遇的憂郁者比比皆是,而「才」不過是可「遇」的先決條件,可被賞識的認可,很難說是大展宏圖的願景,還是一步登天的快感。淡泊名利的隱士們也非清高,只是要決裂這單一的附屬,要靠一個人,太難。如果無法改變環境,又不願被環境改變,唯有逃離一說。很顯然,張藝謀不是隱士,直到今天,他仍然在賣力氣,春晚有他、春節檔也有他。七十三歲的高位者,也難退休啊,拍些令人輕嘆的片子——唉,唉,他為什麼變成這樣了呢?
所幸我們只是普通的觀眾,才能哀嘆一二,在社交平台直抒胸臆,哀婉幾句。只是,張藝謀早已不是電影的導演,他更像是款過期的膠水,正費力黏合電影與中國間的巨大裂縫,如此說來,他早已是個符號了。如今,成熟的電影工業還未成型,甚至困難重重,由此暴露的諸多問題,已不是「張藝謀」這塊招牌能縫合的了。懷才不遇的舊時文人在現代浪潮中很難再騙得淚水,尤其在權利意識不斷高漲後,對經由傳統建構的神聖意義的清算也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我們需要新的電影,可苦尋不得,反而多了很多新造的電影。也算一種怪誕的奇觀了。
(二)
而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人,張藝謀身上的爭議也是復雜的。
從八八年在西柏林一舉奪魁後,後殖民的批評聲就一直籠罩著張藝謀。若已經有了黑澤明與阿巴斯,為什麼還需要張藝謀?這是我看《紅高粱》時貫穿全片的疑問。旺盛的生命、親密的土地、堅韌的氣節。在獻祭式的抵抗後,一輪鮮紅的赤陽從遠處緩緩落下,懸在高粱涌浪上,天地一片血紅。這群赤身光膀的漢子身上似乎凝結著富餘的酒神精神,那種原生的熱情是被工具理性虜獲的文明社會永遠失去的,於是欣賞、褒獎、認可,在西方的凝視下,古老中國未被馴化的野蠻與土氣讓他們眼前一亮。有評論認為,這是奉承,也是矮化。需要向世界展示一個現代的中國,這才是攝影機這雙眼睛應該看到的。這種觀點不無道理,雖然「未被馴化的野蠻」並非絕對的貶義,只是文明/野蠻這組二元秩序的現實意義幾乎囊括了其全部的價值,「落後便要挨打」,切膚之痛往往最深刻。
不過,西方看待原始(或另一文明的景觀)的態度遠比我們想像的復雜,這一態度也與今天將多元主義塑造成政治正確有著密切關系。可以將其視為一種補償——並非道德意義上的虧欠,而是在意識形態上的贈予。其語義是:其餘文明在現實中均遭到了西方文明的同化而逐漸消亡,那麼在意識層面,給予一些象徵意義的精神認可是必要的——當資產階級在現實的樂園里享受山珍海味時,被壓迫者們只能啃著大白饅頭,盯著視聽語言中的佳餚滿足味蕾的想像。這兩件事之間有一定相似之處。而換種角度去想,那些對於文明批判的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也視「原始」為一個突破口,試圖從哲學意義上摧毀文明的進步性。只是,若無法讓真正的現實有所改觀,依靠奇觀贏得獎項的質疑便一直存在。不過,也不能因此全盤否認早期張藝謀的電影貢獻。必須把語境縮小,對准大陸電影這一范圍,張藝謀的影像實驗無疑是開創性的。第五代導演的集體貢獻在於,他們將現代電影語言落到實踐當中,而張藝謀在其中又是佼佼者。
人們對張藝謀的共識是,他是形式主義大師,卻在劇作上捉襟見肘,使得電影皮肉分離,缺乏內核,只是張華麗的皮兒。這一評價讓我曾想像如果張藝謀一輩子搞實驗電影會如何,他或許會成為標新立異的另一種先驅。只是,這終究只是想像。之前有人拿張藝謀與李安生涯軌跡作對比,一邊稱贊後者的職業,一邊批評前者的飄忽不定,最終將原因歸咎於體制的不同。誠然如此,也不止如此。正如魯迅先生所言,要有天才之前,必須有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要有這樣的民眾,必須有可以養活天才的土壤。倘若既無土壤,也無民眾,那天才最終要麼夭折、要麼同化、要麼隱姓埋名。可如今的社會論調也有些耐人尋味,一面要求天才的出現,卻絕不給他成長的空間。第一部作品出來若不盡如人意,先罵為敬;若出彩至極,就捧上天,大誇特夸。可爭議是免不了的。在今天,已不可能有一部作品滿足所有人的喜好,作者們必須明白,創作要麼迎合一類人,要麼只為自己創作,可都容易走了極端,於是哪一類能填飽肚子,哪一類就是最佳選擇。如此看來,張藝謀與李安是真幸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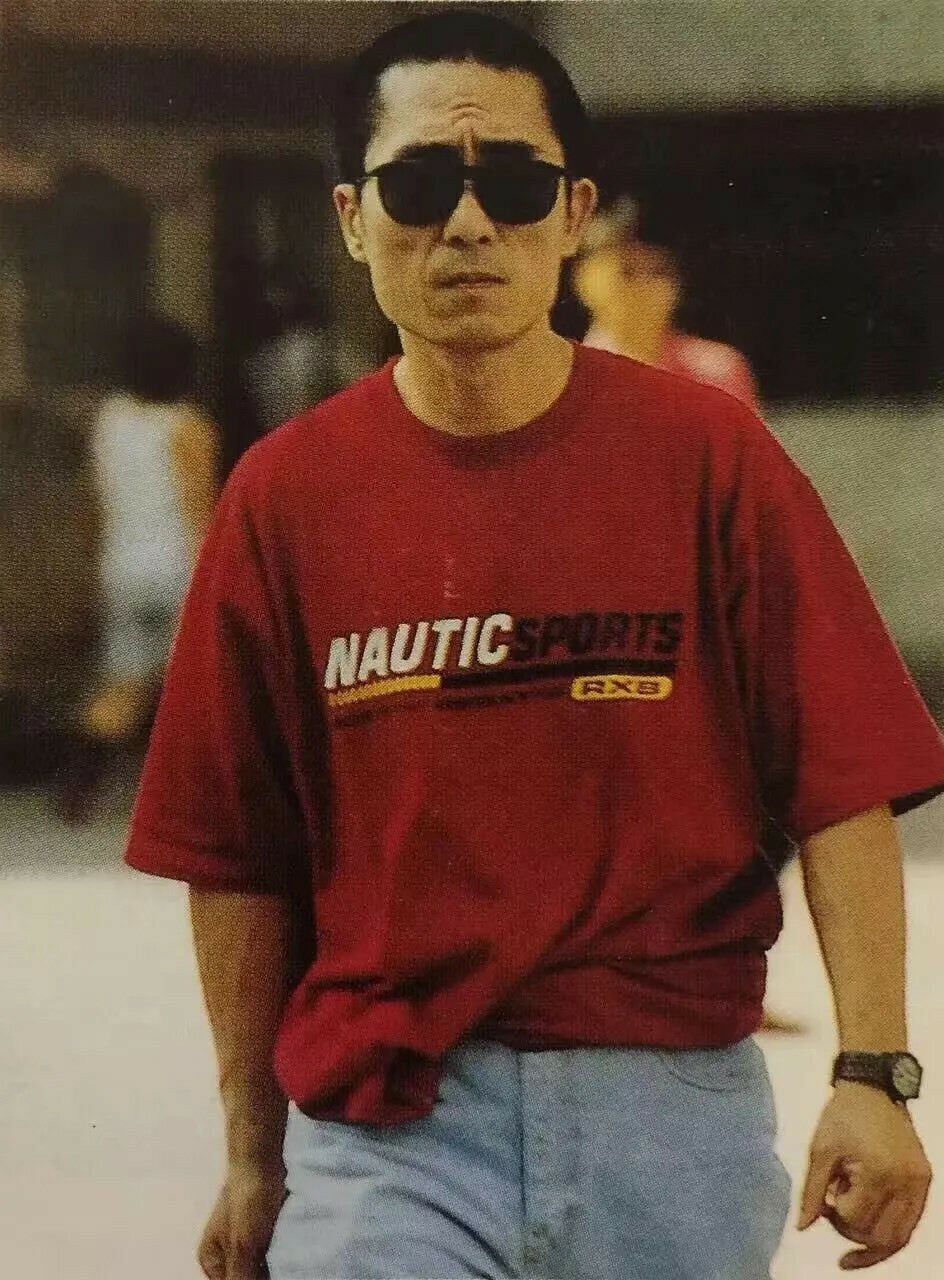
來源:機核
